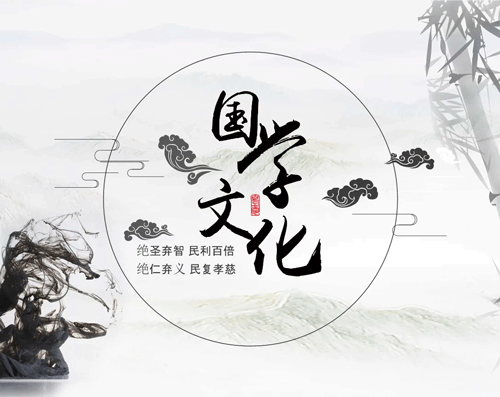夺人丈夫
发布时间:2023-10-26 11:22:12作者:药师网夺人丈夫
异国他乡,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在学毕业,我被分配到这个与俄罗斯毗邻的边境小城旅游局做了一名俄语翻译。国庆节前夕,我带团到俄罗斯滨海边区哈巴罗夫斯克观光旅游,在那个风光旖旎的民异国城市,我认识了林暖。
林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含辛茹苦把他和两个姐姐拉扯大,但在缺少母爱的家庭里,林暖像很多单亲家庭里的孩子一样走过歧路。15岁那年,他瞒着父亲偷偷地退学了,整天吊儿郎当地和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混码头。后来,父亲一位搞建筑的世交不忍看到他如此颓废下去,便把他带在身边开始走南闯北承包建筑工程。15年后,他凭借自己的聪明和魄力在东三省建筑行业站稳脚,拥有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建筑工程公司。他的公司在俄罗斯滨海边区名气很大,这是他的公司第三次来哈巴施工。
认识林暖以后,为了能经常和他见面,我没有放过任何一次到哈巴罗夫斯克旅游观光团的翻译工作。远东艺术博物馆、SKV---画廊、“维金格”迪斯科俱乐部,处处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的初恋在异国他乡如破土的春芽般疯长起来。
林暖经常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和那充满艰辛的创业史,他那坎坷的人生经历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他幽默的谈吐,成熟稳健的性格,风流倜傥的外型,不卑不亢的处世之道,他的一切一切无不让我着迷。尽管他比我大10岁,有家有室,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地爱上他。
不久,林暖在哈巴承包的工程竣工了。回国之后,他经常开6个多小时的车到我居住的小城来看我,一束束鲜嫩欲滴的红玫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一套套高档时装和精美的首饰,把我这个刚刚走出校门的丑小鸭打扮成一只高贵的白天鹅。那段日子我被他宠得失去了自我,我深深体会到了被男人爱的幸福。
可是好景不长,他的妻子知道了我们的关系。她领着女儿坐长途车到旅游局找我。看见我她还没有张口,眼泪就顺着那张苍白憔悴、眼角已隐约可见一道道鱼尾纹的脸流下来。她求我离开林暖。她说:“我们这些年吃了很多苦,刚刚过上好日子没多久。我女儿刚5岁,看在孩子的份上。”我当时很尴尬,不容她说完,就不耐烦的打断她:“面子?你都找到我单位来了,你给我留面子了吗?”一直在她身边死死地抓着她衣襟小声哭泣的女孩,被我吓得哇哇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嚷:“妈妈,回家吧。”她们娘俩在旅游局院子里哭成一团,引来很多单位同事站在旁边看热闹。我气得浑身抖。林暖接到我的电话赶来时天已经黑了。他推开车门直奔他的妻子走过去,二话没说,抡起拳头劈头盖脸地朝那个眼睛哭得红肿的女人打过去。他的女儿在一旁用小拳头一边打他一边哭喊:“爸爸,爸爸,求求你别打妈妈。”看着那个蹲在地上用双手紧紧护着头的女人,我的心里竟然隐隐有一丝快感。
这件事过去后不久,林暖的妻子又给我打过两次电话,每次我一听是她的声音就把电话挂断。又过了大约20多天,那个和林暖一起生活了8年的女人,带着女儿和分得的财产离开了已经移情别恋的丈夫。拿到离婚证当天,这个刚刚冲出围城的男人就在“蓝调”酒吧向我求婚。
我抛开一切,和他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我是个黑户,因为我的户口留在父母那。在那套一百多平方米、装饰得格外豪华的新房里,林暖按捺住第二次做新郎的喜悦,动情地对我说:“等过一段时间工地不忙了,我再给你把户口调过来,到时候把结婚证一起办了。”沉浸在幸福之中不能自拔的我毫不犹豫地点点头。

没想到,我这一等就是9年。
相煎何急,表妹抢走了他的心。我从来没有怪芳菲引诱他。芳菲是我一个远房表妹,比我小10岁。在一般人眼里,她是个浑身散发魅力的花季少女,她的聪明、心机让人对她欲罢不能。还在读师范学院时,她对身边数十个追求者熟视无睹,出人意料地把全校师生公认为老实本分、比她大8岁的班主任搞定,在师范学院引起了轩然大波,没有人知道她是为了什么。临毕业前,她把已经离了婚的老师一脚踹开了。
毕业后,芳菲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当了一名记者。我那朴实得有些木讷的表舅不远千里来找我,他千叮万嘱,让我看在老一辈人几十年交情的份上多关照关照他这个女儿。
我敢说,当我领着芳菲走进家门那一刻起,林暖和芳菲不开始眉目传情了。他用夸张的口吻恭维她:“在我们市的记者队伍里,像你一样才貌双全的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但像你这么年轻的恐怕绝无仅有吧?”在这个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表姐夫面前,芳菲嗲声嗲气地笑着要林暖多关心自己,那笑声让我的心跳有些加速。
没多久,直觉告诉我林暖的心被芳菲俘虏了,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他的跑车里有芳菲惯用的“圣罗兰”香水味道,他的手机上有芳菲发给他的短消息,我甚至在他的车上拾到芳菲遗落的耳钉。我问,他否认。他懒懒地靠在沙发上,用手摸着刮得铁青的下巴:“芳菲就像电话旁边那盆花。”说罢,他坐在那里阴阳怪气地笑起来。望着电话机旁边那棵他一直称之为“小妖精”的文竹,我不由分说地发了脾气,让他以后离芳菲远一点。
但是我发现芳菲来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的床上有她的头发,我的水杯口有她的唇彩,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她的痕记。一天,热心的邻居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要看住你老公和你的小表妹,我看他们的关系不同寻常。”但是信奉家丑不可外扬的我,连着假笑掩饰说,“不会的,我表妹性格比较外向而已。”可关上家门,我和林暖开始无休止地吵架,每一次吵架我们都会大打出手。我的身上经常会留下一块一块瘀紫的伤痕。伤很痛,可我的心更痛,在这个城市里,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心里的苦没法向人倾诉,另外,女儿还小,我不想让她过早地知道大人之间的纠纷,所以无论怎样我都要维护我的这个家。
一天, 菲很早就来到我家。趁他还没有回来,我委婉地对芳菲说:“芳菲,我们是表姐妹,按理说,我不应该怀疑你和你姐夫之间能发生什么。”没容我把话说完,芳菲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历声喝道:“你不要自己没有羞耻心,就以为别人也不要脸。”说完摔门而去,很久我都没有回味过来她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零点的钟声刚刚敲过,林暖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一进门,脱下一只皮鞋“嗖”地朝我扔过来,然手摇摇晃晃地冲我扑过来,一边骂一边用脚踹我,这些日子里所有的积怨顿时涌上来,心里几乎要爆炸,我不顾一切地和这个一起生活了8年的男人滚做一团,拼命厮打起来。
那天晚上,家里书房的门被砸破了,组合音响摔得七零八落,厨房中的餐具打得粉碎。为了保全那台笔计本电脑,我的头上、身上被他用菜刀砍了4刀。血顺着脸颊一滴一滴地滴落在睡衣上,感觉又凉又粘,那一刻我的心冰凉。
跟他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辈子注定是某栋屋里默默无语的主妇,我当初很开心地选择了这条路,我信任他,但我没有想到现在的情形会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于刻意回避这些创痛,但看到在丈夫面前娇嗔的妻子,在父母身边嬉戏的孩子,我还是禁不住心如刀绞。我不知道,这个我认识了9年、在一起共同生活了8年的男人什么时候竟变得如此陌生,还是当初我根本就没有认清他?
母亲、大姐和姐夫听到消息后没敢告诉患心脏病的父亲。他们编了一个理由急急忙忙赶来看我。姐夫给林暖打了5个电话他才回来。他紧绷着脸,在我家人面前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态,任凭我家人说什么,他就是一言不发。
母亲和姐夫试图说服林暖好好过日子,他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无动于衷。我感觉门外有人在不停地走动,就打开了防盗门,只见林暖的两个徒弟一人手里拎着两个啤酒瓶子站在门外。他们满脸愕然地盯着我头上缠的绷带,其中一个叫小东的男孩迅速地把双手背到了身后,不好意思地叫了我一声:“师母。”看着在屋里一言不发的林暖,看着眼前拎着酒瓶子的男孩,突然间我醒悟到,林暖是让他们来做帮手的,以防万一要和我家人打架。他只想这样解决问题?那一刻我脑袋里一片空白,当场晕了过去。
林暖那些天一直没回家,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到公司去找他,员工说他去云南大理出差,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母亲、姐姐和姐夫要走了。已年近6旬的母亲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地抹眼泪。看到他们满脸的伤心,我故作轻松地说:“放心吧,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不用担心我。”
苦不堪言,我的忏悔有谁听。林暖从云南回来了,我看见他的车泊在一家叫做“夜上海”的豪华酒吧前。弥漫着朦胧、神秘、奢华情调的酒吧内,林暖的脸上带着我久违的笑容,正眉飞色舞地对他身边几个要好的朋友说着什么。芳菲依偎在他身边时不时地掩嘴而笑。
我的出现并没有让他们有丝毫恐慌,当着朋友的面,林暖很绅士地把斟满暗红色葡萄酒的杯子举到我面前,抿着嘴,挑衅似的乜斜我。我接过酒杯,对茫然看着我的芳菲说:“总有一天,你会为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而后悔。”说完,我扬手把酒杯里的液体泼到仍旧在一旁装绅士的林暖的脸上。林暖一怔,被酒精烧红的脸扭曲着有些变形,随手抄起桌子上一个酒瓶“嗖”地站起身来想打我,他的朋友连忙拦住。在他一声接一声不堪入耳的国骂声中,我扬长而去。
晚上,沉睡中的我被一身酒气的林暖拉下床一阵拳打脚踢。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他像一头失控的野兽扑在我身上咬起来。五岁的女儿跪在床上,一边哭一边喊:“爸爸,爸爸求求你别打妈妈!”已经没有力气挣扎的我蜷缩在床角,任凭这个在一起共同生活了8年的男人折磨我。他打累了,摇摇晃晃地去了卫生间。懂事的女儿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锁上卧室的门,然后,她跪在我身边,一边哭一边摇晃着我的胳膊:“妈妈,妈妈我害怕爸爸,明天我们去姥姥家吧。”我心如刀绞。转眼,他在门外一边骂一边用传真机砸门,一会儿功夫这个家里唯一完好的门上砸出一个洞。他拉下屋里的电闸,屋子里黑漆漆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林暖的心理有些变态。他在那个破洞前“啪”地点燃打火机,忽明忽暗的火光把他的脸映得极其恐怖。女儿钻进我怀里紧紧地搂着我,歇斯底里地哭喊着:“爸爸,求求你别进来,我怕。”那一刻,我只有一种感觉-----窒息。
那段时间我的身体糟透了,经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个人瘦了一圈。望着镜子里自己那张憔悴的脸,我恨恨地说:“活该!这都是报应。”经受了这么多折磨后,我开始反思,特别是将心比心,想到当年被我拆散了的家庭,想到那对哭倒在我面前的母女,我就十分后悔。我真恨自己当卑鄙地充当了第三者的角色,良心上背了个大包袱,自己也没有得到想像中的幸福,有苦说不出。
他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回家了。这期间我打电话给他,他也从来不接。我去他施工的工地找他,他不是不在,就是看到我的身影一走了之。那段时间芳菲也像人间蒸发了似的,一直没有露面。后来,表舅打来电话,他无比自豪地对我说:“芳菲找了一个有钱的男人,今年7月份就要结婚了。那个男人在江滨公园附近给芳菲买了一别墅正在装修,你抽空去看一看,这个表妹还得让你费心了。”“表舅,快别这么说,一家人客气什么。”我强压住心中的痛苦和表舅说着。对这位从没走出村子的表舅我什么也不想说,我什么都不愿意提起,我一个人成受就足够了。
我在公用电话亭给他打手机,他没想到是我,接通了电话。我说“想和你谈一谈。”我说:“尽管吵过闹过,我还是很在意你和这个家。你所做过的一切我都不追究,回家吧,我求你了。”他在电话那端冷笑。
我哭了:“难道我们真要走离婚这条道吗?我哪里做得不对,你对我说,我改行不行?你说过今生今世和我在一起,你说过永远不会辜负我”“你少胡说。离婚?谁跟你结婚了?证据呢?”他啪地关掉手机。
领着女儿站在那所豪华别墅的大门外犹豫不决,我不知道见到芳菲应该说些什么?我是不是应该跪下来请求她离开林暖?就像此时此刻我想起9年前领着女儿找我的那个女人。
9年了,这个报应早晚还是来了,而且来得那么准确那么残酷,让我无话可说。
那辆黑得泛光的“奥迪”从我们母女身边疾驰而去,车内,他拥着幸福的芳菲开怀大笑。女儿摇着小手大喊:“爸爸,爸爸。小姨,小姨。”我蹲在地上抱住女儿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