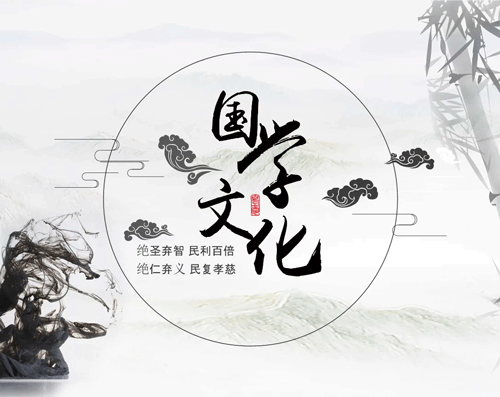酒肉和尚现象试释
发布时间:2023-08-31 13:32:13作者:药师网
“酒肉和尚”一词的出现实际是佛教戒律中国化后的产物,其本身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该词的含义也从其最初的带正面、肯定的意味转到了负面、否定意味,反映了佛教戒律与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文中重提酒肉和尚的相关的历史,对佛教以及其它信仰体系与当今现实道德规范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北朝自梁武帝颁断酒肉文起,中国佛教在戒律上增添了一项新内容,此后时有所谓酒肉和尚的形象在文字记载中出现。唐宋之间则又有一个转折,即文字中的酒肉和尚形象日益被全面否定。这些现象都和社会经济发展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有关。虽然对中国佛教中的素食问题早有不少学者述说过,但较少以“酒肉和尚”形象的演变来作为入眼点,故以此文试释之。
所谓酒肉和尚顾名思义即是吃酒肉的和尚。这种和尚的形象自南北朝起,开始被当时人注意而着墨于史籍。如《魏书》卷十九上《京兆王拓跋太兴传》云:
“初,太兴遇患,请诸沙门行道,所有资财,一时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斋’。及斋后,僧皆四散,有一沙门方云乞斋余食。太兴戏之曰:‘斋食既尽,唯有酒肉’。沙门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只,食尽犹言不饱”。
此僧之所以显得特殊,就是因为他喝酒吃肉。唐初高祖武德年间,“时法琳道人饮酒食肉,不择交游,至有妻子”,也是一样的情况。我们知道,佛教原先的戒律,仅是不杀生,净肉还是吃的,当然酒是“不合饮”的。佛教传入中土后,至南北朝时,梁武帝颁《断酒肉文》,把禁食肉和饮酒相连,一起作为僧尼的重要规范,并“与诸僧尼共伸约誓,今日僧众还寺以后,各各检勒,使依佛教,若复有饮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当依王法治问”,他警告还要把他们:“驱令还俗,与居家(白)衣随时役使”,甚至“若有容受不相举治者,当反任罪”,及“若不禁断,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威胁以国法来强制执行。并在事实上“公私荤菜悉灭除之。又置昭玄十统,肃清正法,使夫二百万众,绥缉无尘”。值得注意的是北周武帝灭法时,他攻击佛教的第二条理由便是:“经律中许僧受食三种净肉,此教不净”。这势必给佛教僧侣们留下长久而深刻的印象,故在梁武帝之后此戒依然成立,并在统治力量的干预下吃素自律成了中国佛教徒的一个特色。
当吃素成为佛教徒,尤其是僧侣的通行规范时,依然饮食酒肉在僧侣中就成为特殊的反常现象。在梁武帝之前则情况恰恰相反,“众僧多不断酒肉”,素食则作为僧侣的高行戒范而被僧史所特写,如释慧力“晋永和中,来游京师,常乞食蔬苦,头陀修福”;还如刘宋时“有释慧生者,亦止龙光寺,蔬食,善众经,兼工草隶”,又如蜀江阳寺释普明“并戒德高,明蔬食诵经,苦节通感”,及释法瑶“年虽栖暮,而蔬苦弗改,戒节清白,道俗归焉”,南齐时也有沙门慧进“蔬食素衣,誓诵《法华》”,“京师龙华寺复有释僧念诵《法华》、《金光明》,蔬食避世”等等。有的还特地声明戒鱼肉。如南齐时僧慧澄“性贞苦,立素斋,戒鱼肉荤辛”,及法云“断鱼肉。验今意行,颇用相符”。后者指法云不食鱼肉与现世相符而颇有先见之明。这也说明当时僧人一般都是吃“净肉”的。所以直到梁武帝时代,僧徒喝酒吃肉才会当作一种异常之状被世人所瞩目而记录于文。这也就是本文一开首说至南北朝方有酒肉和尚形象出现的道理所在。
不过开始见诸于文字的那些酒肉和尚形象,往往并非是以戒律的违背者身份出现。如上文中的两个例子,吃喝酒肉却都成了有异行或神通奇僧的标识了。《魏书·京兆王拓跋太兴传》中那位僧人“及辞出后,酒肉俱在,出门追之,无所见”,从而使京兆王爷更加信佛。后一位法琳道人则能和唐高祖力争,“佛法得全,琳之力也”。还如北魏的释檀特“饮酒啖肉,语嘿无常,逆论来事,后必如言”。
正因为如此,所以亦有个别僧侣将酒肉行来凸现自己。如《宋高僧传》卷四《唐新罗国黄龙寺元晓传》云其“尝与湘法师入唐,慕奘三藏慈恩之门,厥缘既差,息心游往。无何,发言狂悖,示踪乖疏,同居士入酒肆倡家,若志公持金刀铁锡,或制疏以讲杂华,或抚琴以乐祠宇,或闾阎寓宿,或山水坐禅,任意随机,都无定检”。元晓“入酒肆倡家”,当然是一个酒肉和尚的形象了,但这是和他其他殊行一起来表示他的怀志不遇,后来他也据说能“或掷盘而救众,或噀水而扑焚,或数次现形,或六方告灭”,因此这入酒肆倡家依然归于神僧奇行之类。还如五代“晋开运中有僧遇贤,姓林氏,常以酒肉自纵,酒家或遇其饮,则售酒数倍於他,日世号为酒仙,而能告人祸福,必验;与符治疾者,必痊。建隆二年来居是院,创佛屋,修路衢,无虑用钱数百万,虽称丐於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得者。盖其容似灵岩智积圣者,而每与人符,以陈僧为识,或谓为后身”。明代元装,“为嘉福院僧,饮酒食肉,日与儿童嬉戏,市人呼为装颠。每见人即觅酒,醉辄瞋目张拳为金刚之状。见者绝倒”。这元装之状简直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了。
唐代禅宗与密宗的发达,使立地成佛、肉身成佛的观念日益流行,这种观念要求对以往的戒律有新的理解,于是在有关佛教的史料中出现了新的吃酒肉和尚形象。如“唐无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谒於玄宗。玄宗见而敬信焉,因谓三藏曰:‘师不远而来,故倦矣,欲於何方休歇耶’。三藏进曰:‘臣在天竺,常时闻大唐西明寺宣律师持律第一,愿往依止焉’。玄宗可之。宣律禁戒坚苦,焚修精洁。三藏饮酒食肉,言行麤易,往往乘醉喧竞,秽污絪席。宣律颇不能甘之。忽中夜,宣律扪虱,将投于地。三藏半醉,连声呼曰:‘律师律师,扑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异人也,整衣作礼而师事焉”。说明修佛者着意于心中之佛性,而不拘于外在之形式。又据说有人将毒酒给密僧代病喝,“代病执杯啜之,俄尔酒气及两胫足,地为之偾裂,闻者惊怪,以酒供养,自兹始也”。故此类现象在当时愈发普遍,如《太平广记》卷九十四“法将”条载:“法将僧到襄阳。襄阳有客僧,不持僧法,饮酒食肉,体貌至肥,所与交,不择人。僧徒鄙之。见法将至,众僧迎而重之,居处精华,尽心接待。客僧忽持斗酒及一蒸豚来造法将。法将方与道俗正开义理。共志心听之。客僧迳持酒肴,谓法将曰:‘讲说劳苦,且止说经。与我共此酒肉’。法将惊惧,但为退让。客僧因坐户下,以手擘豚裹而飡之,举酒满引而饮之,斯须,酒肉皆尽,因登其床且寝。既夕,讲经僧方诵《涅槃经》。醉僧起曰:‘善哉妙诵,然我亦尝诵之’。因取少草,布西墙下,露坐草中,因讲《涅槃经》,言词明白,落落可听。讲僧因辍诵听之,每至义理深微,闻醉僧诵过经,心自开解。比天方曙,遂终《涅槃经》四十卷。法将生平所疑,一朝散释都尽。法将方庆希有,布座礼之,比及举头,醉僧已灭。诸处寻访,不知所之”。还如唐贞元时有一号称广陵大师的僧人。“好以酒肉为食”,并“好屠犬彘,日与广陵少年斗殴,或醉卧道旁”。有老僧对他说:“僧当死心奉戒,奈何食酒食,杀犬彘”等等?他竟“怒骂曰:‘蝇蚋徒嗜膻腥耳,安能如龙鹤之心哉!然则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岂若汝龊龊无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词”。有一天,“群僧来,见大师眉端之光相,指语曰:‘吾闻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师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於庭,候谒广陵大师。比及开户,而广陵大师已亡去矣。群僧益异其事,因号大师为大师佛焉”。五代时“酷嗜彘肉”的释王罗汉具有“出言若风狂,后亦多验”等神通,被吴越国王敬为“密修神化尊者”。后三个故事不仅显示着神通,还例证了立地成佛和肉身成佛。这里饮食酒肉却成了不可或缺的故事陪衬。
以上所述之吃喝酒肉类和尚并非是后来意义上的酒肉和尚,大体上都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渲染他们的怪诞之处,一方面是为了显凸一些奇僧神僧的特殊点,即所谓“将逆取顺之由,反权合道之意”。所以这类故事多收在诸高僧传的神异篇或感通篇中;另一方面,实质上也是为少数以饮食酒肉犯戒的僧尼作辩解掩护,即所谓“菩萨不习食肉,为度众生示现食肉,虽现食之,其实不食”,从而在民间维护整个僧团的形象。饮酒食肉现象既然有损于佛教及其社会作用,也就不仅仅是佛教自己的事,故有前文所引梁武帝《断酒肉文》中对那些“僧尼若有饮酒噉鱼肉者”的警告。不过此后僧徒中违戒的现象可能不太显着,文献里反映的社会舆论对此种现象的指责也就相对的少。
但是唐宋之间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从下面的二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体察到其间在观念上的一些差异。一是《酉阳杂俎?续集》卷七“金刚经鸠异”云“荆州法性寺僧惟恭”和灵岿因他们“不拘僧仪,好酒,多是非,为众僧所恶”,而被称“一寺二恶”。后来灵岿据说见惟恭因勤念《金刚经》而免地狱之苦,受感悟而“折节缁门”。这除了宣扬诵《金刚经》能抵销违戒饮酒的罪责外,还表达了对那些饮酒食肉僧人回头“折节缁门”的期企。二是《宋高僧传》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窥基传》中有二段故事,先云玄奘三藏欲度窥基,“基亦强拒。激勉再三,拜以从命,奋然抗声曰:‘听我三事,方誓出家。不断情欲、荤血、过中食也’。奘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佯而肯焉。行驾累载前之所欲,故关辅语曰‘三车和尚’。即贞观二十二年也。一基自序云:‘九岁丁艰,渐踈浮俗’。若然者,三车之说,乃厚诬也”。又云窥基后来,“行至太原传法,三车自随,前乘经论箱袠,中乘自御,后乘家妓女仆食馔。於路间遇一老父,问乘何人。对曰:‘家属’。父曰:‘知法甚精,携家属偕,恐不称教’。基闻之,顿悔前非,翛然独往。老父即文殊菩萨也。此亦卮语矣。随奘在玉华宫参译之际,三车何处安置乎”?同一传记里两次提到此事,足见《宋传》作者赞宁辩护心切。但是,第一,这个传说在当初一定流传很广,所以有不同的故事版本;第二,不管事实究竟如何,传说中窥基当时能够如此提出或做,玄奘也同意了他,除了后来那个文殊菩萨的化身外,似乎也没有什么人阻拦或指责他。那时人们对此好象并不很在意,很可能是将此作为高僧的奇行来看待,那时是在唐初。赞宁作《宋传》时已是北宋,他一再称此传说为“乃厚诬也”,“此亦卮语矣”,而且也说错了,因为窥基去的是太原,离五台山不远,现都属山西省,所以有文殊菩萨的出现,而玄奘译经的玉华宫在现陕西省,根本不是一回事。赞宁之所以不顾一切辩解之,是因为此“三事”到了宋代已成了不得的大事,不容得一点点含糊了。我们可以据此看出其间观念上的一些变化。
观念变化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因为不管怎么说,饮酒食肉是一种破坏戒律的行为,如果在种种借口下此现象蔓延开来,对佛教的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故禁戒的呼声也随之高涨。但这个问题在唐宋之间起开始显得严重,却是有着一定背景的。首先自中唐以后,土地买卖的公然化带动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商品化,寺院僧侣也都被卷入这个浪潮中。姜伯勤先生考证敦煌卷子后认为,由于“僧官们终日为寺院营利而奔忙”,所以“僧官中缺乏钻研章句的义学家、学问僧;戒律也松弛了”,甚至“一个寺院周围集结了数名酒户”,他们“自寺院领取酒本,并向寺院提供酒供”,给“僧食用”。这可视为商业活动对寺院僧侣的反作用。其次,官方对僧侣数目的控制放松。“卖牒之举,始于唐肃宗”,北宋盛于神宗之后,“南宋则纳钱于官,便可出家”,而“元代重佛,出家漫无限制”,“明代由官给牒,亦常猥滥”,其实清代与明代的情况也差不多。“天下僧尼,不可胜数”[26]造成了僧侣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和尚饮酒食肉现象当然多了起来。再次,唐至宋元,禅、密两宗影响的扩展,似乎给一部分僧人饮酒食肉找到了借口,个别僧侣更是肆无忌惮,正如前面举的一些例子所表明的。最后,唐自安史之乱后,由于多方因素的交错,使得佛教进一步民间化与世俗化,所谓民间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此相对照的不仅是佛学理论的发展裹足不前,而且戒律的严肃性也受到了很大的侵犯。这样,和尚吃不吃酒肉的问题就变得敏感起来,哪怕作为奇僧的殊行也不行了。
与此同时,佛教内部则以各种方式对饮酒食肉行为进行纠察。其一,是对戒律在阐释和实行上进行加强,律宗的形成,禅门清规的制定等当与此有关。其二,借助儒家的礼教思想,如云:“减杀者引儒礼无故不杀牛羊者,皆重其生,去其滥逸也。又云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此即上帝悼损害之失,树止杀之渐也”,来证明不杀生不吃肉是符合儒家传统的,以增强社会支持禁戒的力度。其三,用各种形式,对饮酒食肉现象进行否定。如《法苑珠林》卷五《六道篇?受苦部》云:“若於先世以酒施於持戒之人,或破禁戒而自饮酒,或作麴酿,临命终时,其心迷乱,失於正念,堕於地狱”。又如据说唐东宫参军郑师辩“持五戒后数年,有友人劝食猪肉。辩不得已食一脔。是夜,梦己化为罗刹爪齿,各长数尺,捉生猪食之。既晓,觉口腥,唾出血,使人视,满口尽是凝血。辩惊不敢复食肉”。有一个故事很有趣,“兴元县西墅有兰若,上座僧常饮酒食肉,群辈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饼,招群徒众,入尸陁林,以饼裹腐尸肉而食,数啖不已。众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诸肉’。自此缁徒因成精进也”。表明不是一般僧人都有资格饮酒食肉的,以杜绝各种犯戒的借口。其四,是通过各种途径,直接间接地宣传遵戒守律。如对持戒守律者的颂扬,并且不时地遵守戒律和不食酒肉联系在一起,有的僧侣虔诚地“希有屠猎改业,乃使市无肉肆”。甚至波及居士,如北齐时卢潜“戒断酒肉,笃信释氏”。又如唐代裴休“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这种风气也一直流传至今。
但是不断对僧侣奉戒的表彰和强调,正是此另一个侧面说明僧侣中破坏戒律现象的严重,其破坏的内容中当然也包含着饮酒吃肉。且若这种现象一但多了起来,势必对戒律约束产生冲击性的作用,到了情况严重时,就出现了概括性的酒肉僧之称。如唐代洛阳广爱寺有个不知名的僧人啖饮酒肉,却能将《华严经》诵得“金色光明自僧之口两角出”,于是使其他僧人“亦生羡慕,窃自念言:‘彼酒肉僧,乃能诵斯大经’”。
后来,随着明清两代商品经济发达和佛教在城市中的进一步发展,“酒肉僧”一词也更世俗地转化为市民口语“酒肉和尚”。这首先见诸于明清时的小说家言,如李汝珍《镜花缘》第十四回里林之洋道:“岭上那个秃驴,又吃荤,又喝酒,又有老婆,明明是个酒肉和尚”。陈森《品花宝鉴》第八回云:“那和尚相貌,是个紫糖色方脸,两撇浓须,有四十来岁,戴个绒僧帽,穿件宝兰绸狐皮僧袍,腰拴黄丝绦,足下挖云青缎毛儿窝,也没有出家人的光景,定是酒肉和尚”等等。
必须声明的是,吃喝酒肉的和尚形象在古代笔记小说中早已现身多多。如宋代“庆历中,种世衡守青涧城,谋用间以离之。有悟空寺僧光信者,落魄耽酒,边人谓之‘土和尚’,多往来蕃部中。世衡尝厚给酒肉,善遇之”。五代时陈裕《咏大慈寺斋头鲜於闍梨》诗云:“酒肉中朝没阙时,高堂大舍养肥尸;行婆满院多为妇,童子成行半是儿。面折掇斋穷措大,笑迎搽粉阿尼师,一朝苦也无常至,剑树刀山不放伊”。形象十分生动。但从酒肉僧到更市俗化的酒肉和尚在小说中的出现则是将这类和尚定型化,不仅如此,更是将这种类型的和尚定了犯戒违律,佛门败类之性,完全成了一个贬义词。
小说笔记是社会世情风貌在文字上的重要反馈方式,因此酒肉和尚一词在小说中的屡屡出现,不仅是说明了当时僧界中以饮食酒肉而犯戒背律现象的严重性,而且是整个佛教僧团的道德形象在民众眼里颓落的一个征兆。
宗教作为社会道德的源泉之一,是宗教存在合法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理由,因此道德形象的败坏对宗教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中唐时有一个叫法照的和尚在旅舍公然吃肉,“且无耻愧,旁若无人。客皆诟骂,少年有欲殴者”。僧人吃肉行为在民众里引起如此严重的反应,对佛教的影响简直是致命的。《阅微草堂笔记》卷七中的一则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曩在某寺,见僧以福田诱财物,供酒肉资。因着一论,戒勿施舍。夜梦一神,似彼教所谓伽兰者,与余侃侃争曰:‘君勿尔也。以佛法论,广大慈悲,万物平等。彼僧尼非万物之一耶?施食及于鸟鸢,爱惜及于虫鼠,欲其生也。此辈藉施舍以生,君必使之饥而死,曾视之不若鸟鸢虫鼠耶?其间破坏戒律,自堕泥犁者,诚比比皆是。然因有枭鸟,而尽戕羽族;因有破獍,而尽戕兽类,有是理耶?以世法论,田不足授,不能不使百姓自谋食。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种,募化亦谋食之一道耳。必以其不耕不织,为蠹国耗民,彼不耕不织而蠹国耗民者,独僧尼耶?君何不一一着论禁之也?且天下之大,此辈岂止数十万?一旦绝其衣食之源,羸弱者转乎沟壑,姑勿具论;桀黠者铤而走险,君何以善其后耶?昌黎辟佛,尚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君无策以养,而徒睃其生,岂但非佛意,恐亦非孔孟意也。驷不及舌,君其图之’。余梦中欲与辩,倏然已觉,其欲历历可忆”。

少数僧人吃酒肉,绝大多数僧人就有可能得不到施舍而没饭吃,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戒律就是约束,就是遵行者克制着自己的欲望和利益,由此,也就使宗教成了社会道德的源泉之一,并促动了人们的敬畏与信仰。如果宗教的戒律受到破坏,这意味着它的道德形象也受到损害,由此信奉追随这个宗教的人们就会散去,靠“施舍以生”的僧侣就不能维持生存了。这中间,酒肉作为日常饮食里的重要内容,非常普遍而且极易勾起人的基本欲望,与追求从欲海中解脱的佛教目标相悖,所以构成了对佛教戒律的莫大威胁。
总而言之,“酒肉和尚”是佛教戒律中国化后的产物,其形象的发展既是唐宋间佛教形态变化的一个标识,也是佛教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中进一步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表现。由于它淡化了戒律的严肃性和佛教作为社会道德源泉之一的神圣性,其对佛教来说是远远弊大于利的。因此在佛教日益都市化的今天,考察与总结这段和酒肉和尚相关的历史,对佛教以及其它信仰体系而言,可以说不失为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