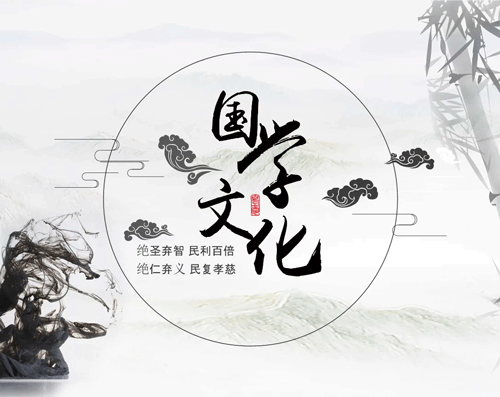与佛学报馆书节录
发布时间:2024-01-24 09:10:05作者:药师网大觉世尊,于无量劫,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以髓为水,流通常住法宝。普度一切众生。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即《四十华严卷第四十》)常随佛学章云:“如此娑婆世界毘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为重法故,不惜身命。……”
圭峰钞释曰:“剥皮为纸等者,有二:一、随相释,二、观智释。且初:或诸缘阙,必要记持圣言,故不惜身命,剥皮析骨;或虽竹帛纸墨不少,要须重法苦身,以展诚敬之志,所以如此也。如集一切福德三昧经云:昔过去久远阿僧祗劫,有一仙人,名曰最胜,住山林中,见诸神仙常行慈心,复作是念:非但慈心能济众生;唯集多闻,灭众生烦恼邪见,能生正见。念已,便诣城邑聚落,处处推求说法之师,时有天魔,来语仙人言:我今有佛所说一偈,汝今若能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析骨为笔,书写此偈,当为汝说。最胜仙人闻已,念言:我于无量百千劫中,常以无事为他割截,受苦无量,都无利益;我今当捨不坚之身,易得妙法。欢喜踊跃!即以利刀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析骨为笔,合掌向天,请说佛偈。时魔见已,愁忧憔悴,即便隐去。仙人见已,作如是言:我今为法,不惜身命,剥皮为纸,刺血为墨,析骨为笔,为众生故,志诚不虚,余方世界,有大慈悲能说法者,当现我前,作是语时,东方去此三十二刹,有佛国土,名普无垢,国中有佛,号净名王,忽住其前,放大光明,照最胜身,苦痛即除,平复如故。佛即广说集一切福德三昧;最胜闻法,得无碍辩。佛说法已,还复不现。最胜仙人得辩才已,为诸众生广说妙法,令无量众生住三乘道;经千岁后,尔乃命终,生净名王佛普无垢国;由敬法故,今得成佛。佛告净威:昔最胜者,今我身是。是以当知:若有人能恭敬求法,佛于其人不入涅槃,法亦不灭,虽在异土,常面见佛,得闻正法,故云剥皮为纸等也。二、观智释者:谓观察此身,若皮、若骨,都无定实,举体全空,无我我所,虽目覩似有之相,而乃如聚沫,如泡,如焰,如芭蕉,既无自体,元同法界。如是一一推征,三谛具足,成空假中之三观;诠此义时,生得此解,契合圆机,便是写经;经是诠表生解义,不观不推,即心迷取相,是无经也。
佛学丛报一书,直使佛法流通中外,含识尽证一乘。
《佛学丛报》,没看过,内容不详。
“含识”,谓含有情识,即众生的异名。亦作:含生、含灵、含情。
但以世俗读书,绝无敬畏,晨起则不加盥漱;登厕则不行洗濯;或置座榻;或作枕头;夜卧而观,则与亵衣同聚;对案而读,则与杂物乱堆。视圣贤之语言,同破坏之故纸;漫不介意,毫无敬容。甚至,书香家之妇女,花册皆是经传;世禄家之仆隶,揩物悉用文章。种种亵黩,难以枚举!积弊已久,习矣不察。若不特示祸福,决定难免亵黩。未曾得益,先获大罪!闵斯无知,须预指陈。
这种情形,实在很多,而且现在此印祖在世时,更增加严重不知多少倍了,令人慨叹不已!
若以愚见:皮面图画,可不必印;名标其傍,如常书式;中间或作伽陀,或作散文,少则数句,多则十余,言须简明,字须粗大,诫令视者,加意珍重,毋或亵污。大觉法王度生妙道,敬则获福,慢则致祸。
尝观弘化社印行的佛书,就是依照印祖所示:标题在傍,中间则书:
“一切佛经,及阐扬佛法诸书,无不令人趋吉避凶,改过迁善;明三世之因果,识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极乐之莲邦。读者必须生感恩心,作难遭想,净手洁案,主敬存诚,如面佛天,如临师保;则无边利益,自可亲得。若肆无忌惮,任意亵渎,及固执管见,妄生毁谤,则罪过弥天,苦报无尽!奉劝世人,当远罪求益,离苦得乐也。”
文极醒目,读之,使人油然而生敬法之心。今时,已看不见这种封面的佛书了!
皮里,宜用小字,详陈:此书虽名报书,实同佛经;而且首有佛菩萨像;内中,或录经文,或宗经义,不同世谛语言,理宜格外敬重。再引经论传记中敬、亵经典,罪、福案证,庶知好歹者,不致仍存故态,误造恶业。此二,或一册一换;或间次一换;或永远不换,只用一种文字;皆无不可,若换,则只可换文,不可换义;则庶乎师严道尊矣。
上文的“皮面”,就是“封面”。“皮里”,就是“封面里”,下文的“书后皮面”,就是“封底”。
也有佛书在封面里印《保宁勇禅师示看经警策文》,其文曰:
“夫看经之法,后学须知。当净三业;若三业无亏,则百福俱集。三业者,身、口、意也。一、端身正坐,如对圣容,则身业净也;二、口无杂言,断诸嬉笑,则口业净也;三、意不散乱,屏息万缘,则意业净也。内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于真源,庶研穷于法理;可谓水澄珠莹,云散月明;义海涌于胸襟,智岳凝于耳目。辄莫容易,实非小缘。心法双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报佛恩。”
书后皮面,不可印字,以免涂污,而昭敬重。
今时的佛学书刊,甚至有在封底印上佛像的,怎能免于“涂汙”?真是毫无敬心,其过重矣!
西天二十一祖婆修盘头尊者,自言往劫将证二果,因误以杖倚壁画佛面,遂全失之。吾谓:二果尚失果位,若是凡夫,则永失人身,常处恶道无疑矣!譬如巨富犯大辟,尽家资以赎死,贫人则立见斩首矣!事载“传灯录”二十祖闍夜多尊者章。故知亵慢,其罪非小。
传灯录,即“景德传灯录”,三十卷。宋、道原禅师纂。二十祖章,见卷二。传灯录,见大正藏第五十一册。
乾为大父,坤为大母,四海内外同是同胞……因兹古今来大圣大贤,无不归心而崇事焉。
这一段文——四九三字,请自查文钞原文读之。今略。
世出世间之理,不出“心性”二字;世出世间之事,不出“因果”二字。
“心性”,谓不变之心体(性即体也),即如来藏心,自性清净心;真如自性,真心理体。大乘起信论云:“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止观大意曰:“不变随缘故为心,随缘不变故为性”。心性二字,诸家解说不同,惟宗门则多不区别,如黄檗禅师传心法要曰:“心性不异,即性即心,心不异性。”又曰:“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今此总指诸法之理体而言。
众生沈九界,如来证一乘,于心性毫无增减;其所以升沉迥异,苦乐悬殊者,由因地之修德不一,致果地之受用各别耳。
因者能生,果者所生;有因则必有果,有果则必有因。止观五曰:“招果为因,克获为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是因,如是果,丝毫不爽。大《涅槃经》曰:“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此生空过,后悔无追!”
阐扬佛法,大非易事:唯谈理性,则中下不能受益;专说因果,则上士每厌闻熏。
弘扬佛法,实在很难。谈理、则中下不能受益,说事、则上士厌闻,这是约机而说。而弘法者,似亦有此情况:我曾闻某弘法之士说:“事相浅经,我不会讲。”这大概是专弘“上士”之法,而“入理深谈”就是他的专长吧。可是、也有人学了几十年佛法,还不会“谈玄说妙”,只会“讲故事”,未知“中下”能否“受益”?
此书、科分十门,法不一律,正好事理并进,顿渐齐驱,庶得三根普被,利钝均益。
“此书”,指“佛学丛报”。不曾看过,不知其“十门”为何?
宜将古今来、由学佛得力,发之而为大忠、大孝,纯义、纯仁之事迹,与夫恭敬三宝、谤毁三宝之祸福,及高人淑世道俗之嘉言,戒杀放生之至论,于后数科,册册登载,则愚夫愚妇有所禀承;而通方哲士,因悟理而亦欲实践,从兹不敢摇头掩耳,更急急于愿乐欲闻也。
这是指示该报的要语。编行佛刊者,当可依行。
然因果心性。离之则两伤,合之则双美。故梦东云:“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势所必然也”。
“梦东”,即彻悟大师,事迹见第三十九页。所引文字,出“梦东禅师遗集”卷上“法语”。兹录所引全段原文如下:
“真法无性,染净从缘;一真既举体成十界,则十界全体即一真。是故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势所必然也。”
而末法众生,根机陋劣;禅教诸法,唯仗自力,契悟尚难,何况了脱?唯有仗佛力之净土法门,但具真信切愿,纵五逆十恶,亦可永出轮迴,高预海会。
观无量寿佛经云:“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具诸不善。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应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如此愚人,临命终时,遇善知识,种种安慰,为说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如是至心,令声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终之时,见金莲华,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灵芝疏云:“令念佛者,作观想也。心观为念,口诵为称。”
此不可思议之最上乘法,宜理事并谈,诫劝齐施;震海潮音,霈大法雨;破鲁川辈之邪执,续莲池等之法脉,俾普天同受佛法之益,庶大地悉感诸君之德,则法满寰宇,世复唐虞,道通天地有形外,恩徧飞潜异类中矣!
“破鲁川辈之邪执,续莲池等之法脉”:云棲(莲池)大师遗稿卷一,有“答苏州曹鲁川邑令”书二篇。初篇从略。兹节录次篇、莲池大师答中数段,可知鲁川所执之一斑。
“辱惠书,累累及二千言,玄词妙辩,汪濊层迭,诚羡之、仰之!然窃以为爱我深而辞太费也。果欲扬禅宗抑净土,不消多语,曷不曰:三世诸佛被我一口吞尽;既一佛不立,何人更是阿弥陀?又曷不曰: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既寸土皆无,何方更有极乐国?只此两语,来谕二千言,摄无不尽矣!
又、来谕谓:不了义经乃谈说净土;而以行愿品、起信论当之。起信且止。行愿以一品而摄八十卷之全经,自古及今,谁敢议其不了义者?居士独尚华严而非行愿,行愿不了义,则华严亦不了义矣!
又、来谕谓:楞严取观音、遗势至,复贬为无常生灭。则憍陈如悟客尘二字,可谓达无常、契不生灭矣,何不入圆通之选?诚曰:观音登科,势至下第。岂不闻龙门点额之喻,为齐东野人语耶?又、来谕谓:必待花开见佛方悟无生,则为迂迟。居士达禅宗,岂不知从迷得悟,如睡梦觉,如莲华开?念佛人,有现生见性者,是花开顷刻也;有生后见性者,是花开久远也。机有利钝,功有勤怠,故花开有迟速;安得概以为迂迟耶?
刻论佛法式微,实不在于明末。明季垂中,诸宗悉衰;万历以来,勃然蔚兴:贤首则莲池、雪浪,大振圆宗;
或谓中国佛教至明朝末就衰微了。其实不然。明代中叶,各宗悉衰;到了明神宗万历以后,忽然兴盛起来,各宗都有高德出现。贤首宗,则有莲池大师,雪浪大师,大振圆宗。
莲池大师,教弘贤首,行归净土,前面已说过。
雪浪大师,讳洪恩,字三怀。号雪浪。金陵黄氏子。性颖悟,耽静寂。儿时便学趺坐。双目重瞳,高颡广颧,大口方颐,肌理如玉。年十三,从父往报恩寺听无极湛公讲法华,至“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仿然有觉,遂留不去。他日,母思之切,促父往携之,父至,强之再三,师于袖中密藏剪刀,潜至玄奘三藏塔前,自剪顶发,与其父,曰:将此寄与母。父恸哭,师视之而已,遂为沙弥。精通内典,博综外书,旁及晋字唐诗,乃曰:不读万卷书,不知佛法。其说法,则尽扫训诂,称性而谈;恒教学人,以理观为入法之门;每当敷演,闻声向化,日盈万指。说法三十年,不立壇场,不设高座,一茗、一炉,据几清谭,嬗嬗动听。万历二十六年,主南京大报恩寺,躬率徒众,重新塔像,事成而去。晚岁,于望亭结茆饭僧,躬自执作,亲领学人,日则斋饭,晚则澡浴,夜则说法,二利並施,从化者众。未几,示微疾,一日,告众曰:“汝等善自护持,吾将行矣。”弟子问灭后用龛、用棺?曰:“坐死用龛,卧死用棺。相锡打瓶,且莫安排。”言讫,顷即索浴、更衣,端坐而化,寿六十三。其得度弟子,甚多,最著者:巢松浸,一雨润,大弘法化,有“巢口、雨手”之称。师与憨山大师同侍无极湛公,亲如兄弟。憨公尝撰“雪浪法师传”,见“梦游集”三十。
天台则幽溪、蕅益,力宏观道。
弘扬天台教观的,有幽溪大师,蕅益大师。蕅祖,前面已说过。
幽溪大师:讳传灯,字有门,号无尽。衢州(浙江省)叶氏子。少从进贤映庵禅师剃发;随谒百松法师,闻讲法华,恍有神会;次问楞严大定之旨,百松瞪目周视,师即契入;百松以金云紫袈裟授之。生平修法华、大悲、光明、弥陀、楞严等忏无虚日。卜居幽溪高明寺,尝于新昌大佛前登座说法,众闻石室中天乐铿锵,讲毕乃止。所着生无生论,融会三观,阐扬净土法门,又有法语一篇,最为切要。前后应讲席七十余期,年七十五,预知时至,手书“妙法莲华经”五字,复高倡经题者再,泊然顺化。(新续高僧传四集四四)著有:楞严经玄义、圆通疏、维摩经无我疏、阿弥陀经略解圆中钞、净土生无生论,净土法语等行世。
禅宗:幻有下四人,而天童、磬山,法徧天下;
幻有禅师:讳正传,字一心,号幻有。溧阳(在江苏省)吕氏子。年二十二。往荆溪,投静乐院乐庵长老芟染;蒙庵示诲,师遂矢志曰:“若不见性明心,决不将身倒睡。”一夕,闻瑠璃灯华熚爆声,有省。未几,庵公迁化,师直造燕都,谒笑岩宝祖,久之,得法,后入五台山秘魔岩,居十三载。会唐学微太常问道,恳师南还,住荆溪龙池禹门禅院,师风度简易,神观凝肃;以法道为已任,而机用妙密,迥出常情。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西纪一六一四)二月十二日示寂。先一日,有僧自台山来,师与剧谈宿昔。抵暮,索浴。众察师意,恳请遗训,师举所著帽者三,众无语,师抚膝,奄然而逝。世寿六十六。
幻有门下,得法者,四人,即:密云悟,磬山修,雪峤信,抱朴莲。
密云悟:师讳圆悟,号密云。宜与(江苏省)蒋氏子。儿时,喜兀坐,若有所悟。及长,读六祖壇经,深信宗门下事。一日,采薪,见堆柴突露面前,有省。年二十九,依龙池幻有禅师出家,三十三岁祝发。苦修三载,偶过铜棺山,被跌,豁然大悟。万历四十五年(西纪一六一七),继席龙池。此后,历住天台通玄寺,嘉兴金粟山广慧寺,福州黄檗山万福寺,育王山广利寺,天童山景德寺;凡六坐道场,三十余年,弟子逾三万指!崇祯十四年,敕主南京报恩寺,以老病辞。次年春,归通玄。七月三日示疾。七日晨兴。巡阅匠工如平日;及归丈室,语侍者:倦甚!登寝榻,少顷,方起坐,跏趺未竟,泊然而逝。世寿七十七。全身迎还天童建塔。以其最后住持天童,又塔全身于天童,故以“天童”称之。座下得法弟子十二人,各皆弘化一方,故云“法徧天下”。
磬山修:师讳圆修,字天隐。荆溪闵氏子。自幼失怙。向蔬奉母。弱冠,听讲楞严“一切众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惕然知有生死大事,遂投龙池座下,二十四岁得度。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久未有入。一日,偶展楞严,至佛咄阿难此非汝心,蓦然打失本参。继而掩关龙池,力究“云门扇子话”两载,后闻驴鸣,大悟。师风仪磊落,赋性恬退,亲炙龙池一十八载,累命分座说法,皆辞逊。万历四十八年(西纪一六二○),结茅荆溪磬山,值雪封五十余日,炊烟几绝,师于饥禽野兽中,安之晏如。数载,竟成丛林。独念法门衰落,力恢济上纲宗。大阐别传旨趣;四方向道之士,承风踵接,竞喧宇内!崇祯八年(西纪一六三五)九月二十三日示寂,世寿六十一。门下有:山茨际,松际授,箬庵问,玉林琇等。
雪峤信:师讳圆修,初号雪庭,后改雪峤,晚号语风老人。浙江宁波鄞县之江井巷人。俗姓朱。九岁。闻诵阿弥陀经水鸟树林皆宣法音,遂知信向佛乘。二十九,弃家访道,谒秦望山妙祯山主,及莲池大师;后参龙池,室中机契,即获心印。历住径山、开先、东塔、云门等大刹。一日,微疾,书诀众偈曰:“小儿曹!生死路上好逍遥,皎月冰霜晓,吃杯茶,坐脱去了。”命侍者进茶,饮毕而逝。时清顺治四年(西纪一六四七)八月二十六日。世寿七十七。
抱朴莲:师讳大莲,字抱璞,亦作抱朴、抱樸。临安骆氏子。十五祝发。年二十二。于云棲受具。初游讲席;一日,自念:数年以来,于教相旨趣,虽有理会处,生死岸头,全用不著,遂入径山参禅,后依龙池获悟。住湖州净名庵。崇祯二年己巳(西纪一六二九)八月示寂。寿不详。
以上是临济宗高德。
洞下,则寿昌、博山,代有高人。
曹洞宗,则有:寿昌禅师,博山禅师等,代有高人递传,法脉源远流长。
寿昌禅师,讳慧经。字无明。因住寿昌寺,故称寿昌禅师。师,江西崇仁裴氏子。诞时,难产,祖父诵《金刚经》而娩,因名“经”。生而颖异,长貌苍古。九岁,入乡塾,便问:“‘浩然之气’,是个什么?”塾师异之。居,恒若无意于人间世者。年十七。遂弃笔砚,慨然有向道志。年二十一,偶入居士舍,见案头《金刚经》,阅之,不终卷,忻然若获故物。由是,断荤酒,决志出家,父母听之。时,邑之蕴空忠禅师说法于廪山,遂往依之,即其本名曰“慧经”。执侍三载。常疑《金刚经》四句偈,必有指据;偶见《傅大士颂》曰:“若论四句偈,应当不离身”,不觉释然。遂辞廪山,隐峨峰,诛茆以居,誓曰:“不发明大事,决不下山!”居三年,人无知者。阅传灯录,见僧问兴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师罔措!疑情顿发,日夜提撕,至忘寝食。一日,因搬石次,坚不可举,极力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参无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师关!”遂往廪山呈偈,获印可,始许薙发受具。自此服勤左右,日夕温研,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如一日也。万历二十六年,受请,住宝方寺,时年五十一矣。三十六年,住新城寿昌寺。师生而孱弱,若不胜衣;及住山(峨峰)日,极力砥砺自坚,躬自耕作,凿石开田,不惮劳苦,不事形骸;居不闭户,夜独山行,尝大雪封路,绝食数日!出世度人,历住宝方、寿昌等大刹,建庵院二十余所,七旬,尚混劳侣,耕作不息;丈室萧然,惟作具而已。万历四十五年丁巳,腊月七日,师自田中归,谓众曰:“吾自此不复砌石矣。”众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此时在,试问诸人知也无?那事未曾亲磕著,切须痛下死工夫!”诫语谆谆。末后云:此是老僧最后一著。分付大众,切宜珍重!戊午新正十三日,示微疾,遂不食,曰:“老僧非病,会当行矣。”大众环侍,欣若平日。十四日,书辞道俗。十六日,众请留全身,师命荼毘。自作举火偈,令侍者彻宗,唱偈举火。偈曰:“无始劫来祗者个,今日依然又者个,复将者个了那个,者个那个同安乐!”次晨,洗浴毕,索笔大书曰:“今日分明指示!”掷笔端坐而逝。时万历四十六年戊午(西纪一六一八)正月十七日未时也。荼毘,火光五色,顶骨、牙齿不坏。师生于嘉靖二十七年戊申(西纪一五四八)。世寿七十有一。法嗣有博山元来,晦台元镜,见如元谧,永觉元贤等。语录四卷行世。憨山德清大师撰塔铭,见语录卷四。(以上参考正源略集三及塔铭)
寿昌禅师,是明代禅宗高僧,蕅益大师颇仰其高风,如“儒释宗传窃议”云:“禅宗,自楚石琦大师后,未闻其人也。庶几紫柏老人乎!寿昌无明师,亦不愧古人风格。”(见《灵峰宗论》五之三)明代禅师,在蕅祖眼中,除紫柏老人外,仅有寿昌耳!又、蕅祖与永觉禅师书中,有云:“惟老师耆年硕德,坚握寿昌‘不肯’二字心印,不必频呻哮吼,狐犴已为丧气。”(《灵峰宗论》五之二)读此益可知蕅祖推崇寿昌之一斑。
寿昌禅师,虽单提向上,但对于念佛法门,亦有微妙开示。语录中,有“念佛法要”一章,兹录出如下:
“念佛人,要心净,净心念佛净心听;心即佛兮佛即心,成佛无非心净定。
念佛人,要殷勤,净念相继佛先成;佛身充满于法界,一念无差最上乘。
心念佛,绝狐疑,狐疑净尽即菩提;念念不生无系累,十方世界普光辉。
念即佛,佛即念,万法归一生灵焰;灵焰光中发异苗,自然不落诸方便。
念佛心,即净土,净心诸佛依中住;念佛心胜万缘空,空心蚤上无生路。
念佛人,要心正,正心一似玻璃镜;十方明净物难逃,万象森罗心地印。
念佛人,要真切,切心念佛狂心歇;歇却狂心佛现前,光辉一似澄潭月;波澜浩荡不相干,圣凡示现离生灭。
念佛心,听时节,时节到时心自悦;似遭网,打破大散关;如失珠,抒教黄河竭!见有是利不思议,非为饶舌为君说。
念佛心,须猛究,直下念中追本有;非因念佛得成佛,佛性亘然常不朽。剔起眉毛须自看,瞥然亲见忘前咎。
念佛人,有因由,信心不与法为俦;参禅讲解全不顾,直下心明始便休。露地牛,耕翻大地;漫天网,收摄貔貅;生擒活捉威天下,越祖超宗异路头,普劝念佛参禅者,莫把家亲当怨仇!”
──右见《寿昌和尚语录》卷四。
博山禅师:讳元来,字无异。安徽舒城沙氏子。因住博山,世称博山禅师。少学儒典,博览能文。年十六,投五台静庵通和尚出家。修天台教观。越五年,至峨峰,谒寿昌经禅师参究,久之,偶因登厕,覩树上人,大悟。历住信州博山,建州董岩,仰山,福州鼓山,金陵天界等诸大刹。临终时,示微疾,首座进问:“和尚去来自在云何?”师大书“历历分明”,趺坐而逝。时崇祯三年(西纪一六三○)九月。世寿五十六。法嗣有:雪关智誾、宗宝道独、雪磵道奉等。有广录三十五卷,参禅警语二卷,语录集要六卷,行世。
博山和尚参禅警语,最能策励学人的道心,兹录数则如次:“做功夫,最初要发个破生死心坚硬,看破世界身心悉是假缘,无实主宰。若不发明本具的大理,则生死心不破;生死心既不破,无常杀鬼念念不停,却如何排遣?将此一念,作个敲门瓦子,如坐在烈火焰中求出相似,乱行一步不得,停止一步不得,别生一念不得,望别人救不得。当恁麼时,只须不顾猛火,不顾身命,不望人救,不生别念,不暂停止,往前直奔;奔得出,是好手。”
这是开示学参禅者的下手功夫。念佛的人,若能如此下工夫念去,我相信,决能‘屈伸臂顷到莲池’矣。
又云:“做工夫,把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将血肉身心,如死去一般……”
印祖也说:“学道之人,念念不忘此(死)字,则道业自成。”可见无论参禅、念佛,皆要“生死心切”,才能成就。又云:
“做工夫,一日要见一日工夫。若因因循循,百劫千生,未有了的日子。”像如此警语,书中多的是。若能时时阅读,道业必成。
蕅益大师云:“读博山警语,窃喜正法犹在……(博山)大师,乘大愿,具大力,运大悲,扩大量,果与诸方不同……(见“曹溪行呈无异禅师序”,宗论十之一)
第七十六页所云《博山禅师拈净土偈》,此偈有一百八首,首句皆云“净心即是西方土”,见广录卷二十。蕅祖谓此是“以因摄果”,非“以理夺事”,乃作“西方即是唯心土”偈,以补其偏,见《灵峰宗论》十之一。惟博山亦劝赞净土,如《示普周禅者参念佛公案》云:“一句阿弥陀,如珠投浊水;珠投水自清,佛念妄自止。”
印祖所谓“禅宗:幻有下四人,而天童、磬山、法徧天下;洞下则寿昌、博山、代有高人”,用意是在说明:明朝万历以后,禅宗有许高僧耳。
律宗,则慧云中兴,实为优波;见月继踵,原是迦叶。
慧云中兴律祖:讳如磬,字古心。慧云,系神宗赐号。族姓杨,江宁之溧水人。居家时,笃信三宝;年至不惑,有出尘之志,就于摄山棲霞寺礼素庵法师薙发。师步礼五台,历三寒暑,昼夜恳求,一日,于途中忽见一婆子,形枯发白,冠敝衣鹑,手捧僧伽黎,自林而出,问曰:“汝求何事?”师曰:“欲求文殊菩萨,亲授大戒。”婆曰:“持衣来否?”曰:“未。”婆曰:“此衣与汝。”师手接衣,婆去将数步顷,复指曰:“大德!那不是文殊麽?”师一回顾,不见婆子,云中,文殊菩萨垂手摩师顶曰:“古心比丘!文殊为汝授戒竟。”师于言下顿悟心地法门,视大小乘律,恍自胸中流出。自从文殊得戒后,由北还南,中兴戒法;专持梵律,皎若冰霜。万历间,金陵幽棲寺雪浪洪恩法师,奉旨督修金陵长干瑠璃宝塔,诸务严整,唯塔尖艱举,浪法师深以为虑,日夜祈佛慈应,一夕,梦感神谕云:“优波离尊者预斯,始克汝愿。”次日,馨师露顶跣足杖锡偏袒而入,浪师诚恳请助,馨公领众礼佛绕塔,塔尖轻举而辏合;大众见之,莫不忻跃!始知馨公是佛世时持律第一之优波离尊者再来也。神宗敕于五台开壇传戒,赐号慧云。师寂于万历四十三年(西纪一六一五),世寿七十五,法腊二十七,弘戒二十二载,后人尊为中兴律祖。(南山宗统二)
馨公座下,弟子甚多,继师志而弘传戒法者,有三昧寂光律师。光师一生持律谨严,以宝华山为弘戒道场。临终时,前三日,预知时至,鸣楗槌,集众方丈,取紫衣戒本,将华山法席,当众付与见月律师。三天以后,又集众至方丈,取净水沐浴,谓众云:“吾水干即去,汝等莫作去来想。不可讣闻诸方,凡世俗礼仪,总宜捐却。三日后,即葬寺之龙山。”遂命大众念佛,水干、跏趺微笑而逝,时清顺治二年(西纪一六四五)闰六月初四日也。(一梦漫言下)
见月律师,讳读体,字绍如,后更见月。云南楚雄许氏子。母梦梵僧入室,寤而生师。年十四,父母相继弃世,由伯父恩育教诲。师善绘大士像,时人称为小吴道子。二十七岁,伯父逝世,遂发心出家,易道士服,更名真元,号还极,住萧园。除夕夜,梦为僧形,自思后必为僧。三十岁,获读华严经,急欲披剃为僧。八月,朝鸡足山。次年十月,依亮如法师披剃。又次年春,闻亮公诫初出家者云:“出家必先受沙弥十戒,次受比丘戒,具诸威仪,乃名为僧。”师闻之,请求受戒,亮公曰:“吾是法师,受戒须请律师。江南有三昧和尚,大弘毘尼。”遂于四月离师,往参三昧和尚,求受大戒,即开始行脚,自滇南至北方,又从北方至江南等地,跋山涉水,步行两万数千里地,其克苦之精神,真是空前绝后!师之自传——一梦漫言中,载之甚详,有一段云:“又行数日,过盘江,山路屈曲,上下崚险,顷刻大雨,涧流若吼,山径成沟,四面风旋,一身难立。水从颈项直下股衣,两脚横步,如跨浮囊;解带泻水,犹开堤堰;如此数次,寒彻肌骨!……次日至安庄卫道上,砂石凸凹,崚嶒盘曲,不觉履底已穿,脱落难者。即双弃跣足,行数十里。至晚歇宿,足肿无踝,犹如火炙锥刺,中夜思之,身无一钱,此是孤庵野径,又无化处,不能久棲,明早必趋前途。想世人为贪功名富贵,尚耐若干辛苦而后遂;今为出家修行,求解脱道,岂因乏履而退初心?次日仍复强行,初则脚跟艰于點地,渐渐拄杖跛行,行至五六里,不知足属于已,亦不觉所痛。中途又无歇处,至晚将践五十余里,宿安庄卫庵中。次日化得草鞋学著,皮破茧起,任之不顾!”
师于崇祯六年三十二岁离师行脚,三十三岁至宝庆府参颛愚大师,大师新出《楞严四依解》,自如法师代座讲演,(一梦漫言:)“道场圆满,自如法师率众诣五台礼谢,正值大师跏趺伞下,所以别号伞居道人。自如法师礼谢还寺,留余伞下赐饭一餐,其蔬是苦瓜一盘,大师先吃,呼余吃之,其味入口甚苦,不能咽,复不敢吐。大师微笑,谓余云:‘先苦后甜,修行作善知识亦尔。’余礼谢其开示。”笔者初读此书时,即对此“苦瓜味”印象最深,每于饭时得苦瓜,即会影现此段光景于脑际。今趁此机会,将原文录下,与众同享。惜今之苦瓜不但不苦,且已变成甜瓜矣!
次年,闻三昧和尚将于南京古林庵传戒,又赶到古林,言其受戒,知宾云:“若欲受戒,每人攒单银一两五钱,衣钵自备”师以银衣俱无,不得受戒。闻三昧和尚在五台山旧路岭传戒,又到五台,诣方丈参礼,方丈有二僧守门,语云:“有香仪可进,若无,且退。”回堂叹云:“登山涉水,不远数千里而来,今无香仪,不能亲见善知识”!同参成拙云:“不必忧恼,明早守门者去吃粥,自进礼拜。”次早忍饥,直入方丈顶礼,和尚问“汝二人从何来?”答:“从云南来。”又问:“来此作麽?”因无衣钵,不言受戒,但言朝台。和尚云:“文殊在汝,反来朝台,实念修行去!”二人礼谢而出。
崇祯九年,师三十五岁。七月,离五台,改号见月。一梦漫言去云:“逢沟涉水,路错绕道。一日行次腹饥,歇息荒冢树下,谓(同参)觉心云:我等自滇而南,自南而北,今复自北而南,往返二万余里,徒劳跋涉,志愿罔成。披剃师命号绍如者,以冀弘法利生,斯皆绝分,愧之至极!余名读体,体者、身也,乃法身理体;读教以明所诠之理,理明则诠忘;犹因标指见月,月见则指泯;今余改号见月。”次年,师三十六岁。二月初,于丹阳海会庵遇游方僧,告以“三昧和尚 已出北京,正月在扬州石塔寺开戒;今丹徒县海潮庵请,二月初八日起期,何不速去?”即与觉心同到海潮,得圆具戒,满其心愿。
自崇祯十年春,于海潮得戒后,即追随三昧和尚,弘传毘尼。以后,主持华山律席。晚年修过两次般舟三昧。撰有毘尼止持会集,毘尼作持续释,传或正范等。倓虚大师云:“他老一生,无论说话、做事,都非常有刚骨,到处都是唯法是亲,丝毫不徇人情。自出家后,无日不在艰苦卓绝中精进修持。他老的一言一行,无一处不可与后世作模范。”(《影尘回忆录》下册)
清康熙十三年,师七十三岁,因受两序大众请求,述说其一生行脚事迹,以勉将来,乃撰“一梦漫言”。此书,经弘一大师读过,题记云:“欢喜踊跃,叹为稀有!执卷环读,殆忘饮食。感发甚深,含泪流涕者数十次。”乃略为料简,附以眉注,别录行脚图表,冀后学披文析义,无有疑滞。此书,民国四十五年丙申,香港弘法精舍曾印行。倓虚大师云:“过去我对一梦漫言,也阅过几遍,觉得百读不厌!而且在每一次读的时候,使我惭愧万分!含泪欲涕。觉得在操行方面,后人实在不如古人。如果后来人看了这部书不受感动的,那是他没有道心。如果道心具足的话,他一定感同身受,自己惭愧的难过!大家有功夫时,可以把这部书常翻开来看看,很能砥砺自己的道心,祛除自己的习气。裹面不但意思好,文字也好,质朴流畅,一点矫揉造作没有。”(同上)
康熙十七年岁晚,师示微疾;十八年(西纪一六七九),师七十八岁,正月既望,力疾起视,诫弟子曰:“勿进汤药,更七日行矣。”至期,端坐而逝,即正月二十日。荼毘,得五色舍利。以其行迹类摩诃迦叶之头陀苦行,后人谓是迦叶再来,故云:“见月继踵,原是迦叶”。(以上是弘律高僧。)
而妙峰、紫柏、莲池、憨山、蕅益,尤为出类拔萃,末法所不多见。
上文已说过,明朝自万历至明末的台、贤、禅、律、诸宗的高僧;在这些高僧大德中,如:妙峰、紫柏、莲池、憨山、蕅益,尤为出类拔萃,末法时代所不多见的。
妙峰大师:讳福登,妙峰是别号。山西平阳续氏子,春秋续鞠居的后裔。师七岁时,父母逝世,顿失怙恃,为里人牧羊。年十二,投近寺僧出家,不得善视,年十八,遂逃,携一瓢,至蒲板,昼行乞食于市,夜宿文昌阁,阁为山阴王所创,值王游,一见,奇之,谓其五官皆陋——师生而唇掀、齿露、鼻昂、喉结,而神凝、骨坚,乃嘱阁僧曰:当善视此子,他日必成大器。顷之,地大震,民居尽塌,师被压,三日,不死,王闻而益异之。遂修中条山之棲岩兰若,令师闭关以修禅观,师于关中,日夜鹄立者、三年,心有开悟,乃作偈呈王,王见之,曰:此子见处早如此,不折之,他日必狂。因取敝履,割底,封寄之,乃书一偈曰:“者片臭鞋底,封将寄与尔,并不为别事,专打作诗嘴!”师见之,对佛作礼,以线系鞋底,挂于项上。自此,绝无一言矣。出关后,王见师具大人相,甚喜,令往介休山听讲楞严,遂受具戒,时年二十七。后,游南方,徧参知识,至南海,礼普陀,回宁波;染时症,病几死,旅宿,求滴水不可得,乃探手就浴盆,掬水饮之,甚甘;诘朝视之,极秽浊,遂大呕吐,忽自觉,曰,饮之甚甘,视之甚浊,净秽由心耳。即通身大汗,病乃痊。后归中条最深处,诛茆吊影以居,辟榖、饮水三年,大有发悟。王建梵宇于南山,延师居之。每念二亲魂未妥,复觅地迁葬。刺舌血书华严经一部,以报劬劳。万历中,祈皇嗣有应,帝为建华严寺以安之。性善巧思,能建长桥、大像,精巧妙绝,殆人所不能为!又于峨眉、五台、宝华、建铜殿各一,今仍在焉。万历四十年壬子(西纪一六一二),师修会城桥,长十里,工未成,九月,以微疾,还五台山。一日,鸟雀翻飞,绕檐乱鸣,逐之不去,师闻之,曰:百鸟哀鸣,吾将行矣。腊月十九日,端然而逝。寿七十有三。(新续高僧传四集五五、憨山大师梦游集三○、宝华山志五及一二)
紫柏大师:讳真可,字达观,号紫柏老人。吴江沈氏子。性雄猛,状魁伟,少好游侠。年十七,投虎邱僧明觉剃落。尝闭户读书,足不越阃者,年半。凡见僧有饮酒茹荤者,师曰:“出家儿,如此者,可杀也”!时僧甚惮之。既圆具,入武塘景德寺闭关三载,期满游方,闻诵张拙偈:“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大疑之,一日,斋次,忽大悟!乃曰:“使我在临济、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北游京师,参徧融大老,依住九载。万历十七年,于五台创刻方册藏经,后移径山寂照庵。复与憨山议修大明传灯录。二十八年,朝廷榷矿税,宦者乘机四出扰民,师遂入京,思有以解之。每叹曰:憨山不归,则吾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吾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居无何,忽妖书事发,震动中外,忌者乘机构之,遂下诏狱。官鞠之,但以三负对,绝无他辞。时执政欲死师,师闻之,乃曰:“世法如此,久住何为?”索浴罢,嘱侍者曰:“吾去矣!幸谢江南诸护法!”端坐而逝。时万历三十一年癸卯(西纪一六○三)十二月十七日也。世寿六十有一。门人集其遗著,名“紫柏老人集”行世。
紫柏大师,禅净双修;对于念佛法门,亦有微妙开示,兹录其最切要者一二段,以资策勉。
“念佛求生净土之义,义在平生持念;至于临命终时,一心不乱,但知娑婆是极苦之场,净土是极乐之地。譬如鱼、鸟,身在笼槛之内,心飞笼槛之外。念佛人,以娑婆为笼槛,以净土为空水。厌慕纯熟,故舍命时,心中娑婆之欲,了无芥许,所以无论其罪业之轻重,直往无疑耳。倘平生念佛虽久,及至舍命,娑婆欲习不忘,净土观想不一。如此等人,亦谓念佛可以带业往生净土;以义裁之,往生必难。……”(紫柏老人集卷之一)
“僧海州参师,问曰:“汝出家为什麽?“曰:“为求出苦,“师曰:“以何法则求出苦?“曰:“我资钝,但念佛。“师曰:“汝念佛,常间断否?“曰:“合眼睡时便忘了!“师震威呵曰:“合眼便忘,如此念佛,念一万年也没干!汝自今而后,直须睡梦中念佛不断,方有出苦分。若睡梦中不能念佛,忘记了,一开眼时,痛哭起来,直向佛前叩头流血!或念千声,或念万声,尽自家力量便罢。如此做了三二十番,自然大昏睡中,佛即不断矣。且世上念佛底人,或三二十年,或尽形寿念佛,及到临时,却又无用。此是生前睡梦中不曾有念头故也。人生如觉,人死如梦;所以梦中念得佛底人,临死自然不乱也。“”(紫柏老人集卷之四)
民国二十三年,王固存居士读紫柏老人集,尝录出有关念佛者,题曰“念佛槌”,印行于世。其序曰:“余读紫柏大师集,观其语言文字,如千均弩发,皆从心光中喷出,无非指示向上,振扬宗风。即其关于净土启示较少,然莫不言言恳切,字字精悍,简要直捷,妙应时机。余因从其集中摘出此册,以为修念佛者之一助,而名之曰‘念佛槌’。昔紫柏与王宇泰书,有‘见地不透彻,净土岂能亲切?’之语,二林居士谓为‘念佛人脑后一槌’,书以此名也。”今此书未见流通;念佛人,缺此一槌,难怪念佛人多、而往生者少也。
莲池大师,见第二十九页。
憨山大师,见第五十一页。
蕅益大师,见第三十六页。
虽不及唐宋盛时,亦可谓佛日重辉矣!
明代万历初至明末,高僧辈出,盛极一时;虽然不及唐宋,但亦可谓“佛日重辉”啊。
及至大清启运,崇重尤隆。林泉隐逸,多蒙礼敬;如:玉林、憨璞、木陈等。
“大清”,清朝。满洲族爱新觉罗氏兴起后,至太宗(皇太极)即位,始定国号曰“清”。传至世祖(福临,即顺治),入关,代明而有中国。又十传而至溥仪(宣统),以革命军兴,逊位,清乃亡。自世祖至溥仪,凡九世十帝,共二百六十八年;起西纪一六四四,讫一九一一。

印祖谓:清初诸帝,对于佛教,尤为崇重;就是隐逸于林泉的高僧,多有蒙受帝主礼敬者,如:玉林、憨璞、木陈等。
玉林:讳通琇,号玉林(或作琳)。常州(江苏省)江阴杨氏子。天隐修法嗣。修圆寂后,继其法席。顺治十五年(西纪一六五八),受诏入内。十七年,赐号“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康熙十四年(西纪一六七五)八月十日示寂。寿六十二。嗣法弟子二十余人。著语录十二卷。世宗雍正帝御选语录中,录其语要。
玉林法嗣茆溪行森,侍玉林受顺治帝诏,帝请玉林于万善殿升座说法;后迎入西苑,时时问法;遇合之隆,一时无比!之后,玉林还山,帝留行森,问答称旨,赐号“明道正觉禅师”。著有语录。雍正亦录其要于御选语录中。其序云:“朕览玉林父子之书,阐扬宗乘之妙旨,实能利人济世,如杲日在空,迷云顿净;如清钟响夜,幻梦旋消”云云。
憨璞:讳性聪,憨璞、其字。延平顺昌连氏子。十八出家,廿五参方。徧参永觉、天童诸老宿,后依百痴元禅师,即承记莂。顺治十六年已亥,应诏万善殿,赐号“明觉”。康熙五年丙午(西纪一六六六)腊月十三日,书偈毕,掷笔而逝。寿五十七。(正源略集一○)
法系:密云圆悟──费隐通容──百痴行元──憨璞性聪。
木陈:讳道忞,字木陈,号梦隐。潮阳林氏子。薙染于匡庐,具戒于憨山。顺治十六年已亥,应诏万善殿,赐号“弘觉禅师“”康熙十三年甲寅(西纪一六七四)六月示寂,寿七十九。著语录二十卷,北游集(住大内万善殿语录)六卷,布水台集(即文集)三十二卷,禅灯世谱九卷。
法系:密云悟——木陈忞。
世祖遂仰遵佛制,大开方便,罢除试僧,命其随意出家。因传皇戒,制护戒牒,从兹永免度牒矣。佛法之衰,实基于此!
古时要出家,并不容易,必须经过考试及格,才得为僧。如佛祖统纪五一载:唐中宗景龙初,诏天下试童行经义无滞者,度之使为僧。试经度僧,自此始。
所谓“度牒”,是许出家之公验。又名“祠部牒”,以从尚书省之祠部司出之故。隆兴编年通论一六:“天宝五年(西纪七四六)五月,制:天下度僧尼,并令祠部给牒。今谓之祠部者,自是而始。”
至清世祖顺治帝,乃罢除试僧,令民众得随意出家。既免除度牒,出家人,只要有戒牒,就可以到处云游,所谓“天下丛林饭似山,钵孟到处任君馔”。既自由出家,不必考试,久之,难免“良莠不齐”,“龙蛇混杂”。印祖认为清季以来,佛教衰落,实由于此。
在当时,高人林立,似乎有益。
顺治、康熙、雍正、至干隆间,高僧辈出,佛法兴隆,看起来,顺治免除度牒,似有益于佛教。
而世宗以大权乘愿,建中立极,其发挥佛祖慧命之言论,精深宏博;入藏流通者、不必言;外有“御制拣魔辨异录”八卷四册,系吾友子任氏,乞食京师,于书肆中得之,送于杨仁山,命寄东洋,附于新印大藏之内;想其书已出,好古探奇之士,试一读之,不但于性命有益,而学识文章,当顿高十倍矣!呜呼!盛哉!世宗实为法流震旦,皇帝中之绝无而仅有者。其君如此,则宰官、僧侣,概可知矣。
世宗,即雍正帝。其著作,所谓“已入藏流通”者:谅即指“御选语录”,四十卷,龙藏自林字函至即字函。卍续藏第一一九册,作十九卷。
所谓“东洋新印大藏”,谅即指大正藏;但大正藏并无此书。“拣魔辩异录”,在卍续藏第一一四册。扬州藏经院木刻本,前有印祖撰重刻序,此序见印祖文钞卷三:“拣魔辩异录重刻序”及“拣魔辩异录石印序”。欲知此录内容,读此二序可知。此从略。又、雍正七年,尝颁行“大义觉迷录”。萧一山著“清史”云:“至于颁行大义觉迷录、拣魔辩异录,以帝王之尊,和秀才和尚作学术上的辩论,其精神、值得钦佩。”
雍正帝,于禅门,颇有造诣;自谓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于诸公案,总以解路推求,心轻禅宗,谓如来正教,不应如是。自亲近西藏喇嘛章嘉呼图克图,得其启示,乃知向上一事;寻因随喜结七,同坐两日,得洞达本来,方知“惟此一事实”之理;复著力参究,经行次,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复堂中静坐,无为中,忽蹋末后一关,得大自在,受章嘉印可。此时,帝所接近者,尚有迦陵性音。此皆未登位前之事。
帝自号“圆明居士”,尝辑古德语录中之提持向上、直指宗乘者,名“御选语录”;而以自己与人问答言句,收录于第十二卷(卍续卷次)中。帝即位后,当于内廷,提示宗乘,王大臣得其印可者,凡八人,因取所著述,择其合作,编为一集,名“当今法会”,附于御选语录之十九卷。
帝既喜研宗乘,又极提倡净土;盖鉴于禅门空洞之弊,而欲矫正之,示学人以脚踏实地之修行也。其于净土祖师,特提莲池大师,以为模范;御选语录中,采其要语,别为一卷(卷十三),帝自序云:“云棲法汇一书,皆正知正见之说;朕欲表是净土一门,使学人宴坐水月道场,不致歧而视之,误谤般若;故择其言之融会贯通者,刊为外集,以示后世。”──御选语录分正集、外集、前集、后集四类。
帝主张佛、道、儒三教并行;于佛教中,调和教、禅、净;于宗门中,说五家宗旨之一味──语录后序中,性音劝帝研辩五家宗旨,帝谓: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过权移更换面目接人耳。
至于世间法,萧著清史云:“只有雍正帝懂得中国文化精义和孔子的中庸之道,所以他的政治是超乎寻常的。”又云:“他对于清朝的政治,关系甚大,如果没有他,康熙六十年培养的政绩,表现不出来;乾隆六十年的威权,发挥不出来。”可惜他在位不久,仅有十三年。寿五二八岁(据“清史稿”九、世宗本纪)。
迨至高庙以后,哲人日希,愚夫日多。加以频经兵燹,则鄙败无赖之徒,多皆混入法门;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
“高庙”,指清高宗乾隆帝。自乾隆以后,至清末,一百余年间,佛教日渐衰落,僧团龙蛇混杂,且有德真修之出家人少,而“混饭”者多,“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
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这两句语,我当永记在心,不可暂忘。
从兹日趋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致今,僧虽不少,识字者,十不得一,安望其宏扬大教,变利群生耶?
自既不知佛法,何能教徒修行?所以不能宏教利生耳。
由是,高尚之士,除夙有大根者,但见其僧,而不知其道,厌而恶之,不入其中矣!
上来已把清代以来佛教衰落的原因道出。请再参阅后文“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更能了了。
夫流通佛法,非一朝一夕之故。须深谋远虑,随机设法。佛制固不可不遵;而因时制宜之道,亦不可不及及研求,以预防乎世变时迁,庶不致颠覆而不能致力,有如今日之佛法也。倘诸君不乘时利见,吾恐此时震旦国中,已无佛法声迹矣。呜呼!险哉!
宏扬佛法,使佛法在时空中永远流传下去,必须在不违佛制的原则下,通权达变,因时制宜,才能成就。
佛法高深,非浅见所能窥。若欲深知,必须由教而入,次及禅宗,方可无弊。
“必须由教而入”,这是印祖彻底悲心,示人学佛入门途径。下文正明不由教入,直从宗入之弊。
宋儒若周、程、张、朱等,夙世固有灵根;奈最初所亲近者,皆属直指宗师;于一席话、一公案下,仿佛领会得个虚灵不昧,具众理而应万事之意义;实未彻悟自心。遂自以为得,画地自限,不肯前进;良由一向在义路上著脚,绝未会真参力究也。
周敦颐,宋,道州人,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宋神宗熙宁六年癸丑(西纪一○七三)逝世,寿五十七。
居士分灯录下云:濂溪初见晦堂心禅师,问教外别传之旨,心谕之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裹打点,孔子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毕竟以何为道,夕死可耶?颜子不改其乐,所乐何事?但于此究竟,久久自然有个契合处”。又扣东林总禅师。后谒佛印了无禅师,于言下有省。尝叹曰:“吾此妙心,实启迪于黄龙(祖心),发明于佛印;然易理廓达,自非东林开遮拂试,无由表裹洞然”。是谓“最初所亲近者皆属直指宗师”。
张载,字子厚,宋,郿县人。宋神宗熙宁十年丁巳(西纪一○七七)逝世,寿五十八。
程颢,字伯淳,宋,洛阳人。宋神宗元丰八年乙丑(西纪一○八五)逝世,寿五十四。世称明道先生。
程颐,字正叔,颢弟,世称伊川先生。宋徽宗大观元年丁亥(西纪一一○七)逝世,寿七十五。
居士分灯录下云:“明道先生,尝曰:‘佛说光明变现,初莫测其旨,近看华严合论,却说得分哓。应机破惑名之为光,心垢解脱名之为明。只是喻自心光明,便能教化得人,光照无尽世界,只在圣人一心之明;所以诸经之先,皆说放光一事。’颢每见释子读佛书,端庄整肃,乃语学者曰:‘凡看经书,必当如此。今之读书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主得?’一日,过定林寺,偶见众僧入堂,周旋步武,威仪济济,一坐一起,并准清规,乃叹曰:‘三代礼乐尽在矣!’……
伊川先生:或问:佛说生死事,如何?颢曰:譬如水上沤。又问:佛说生死轮回,可否?颢曰:此事说有无皆难,须自见得。圣人只一句断尽了,曰:未知生,焉知死?”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人,侨居建州。宋宁宗庆元六年庚申(西纪一二○○)逝世,寿七十一。
居士分灯录下云:诲庵少年不乐读诗文,因听一尊宿谈禅,直指本心,遂悟照照灵灵一著。年十八,从刘屏山游,山意其留心举业,搜之,箧中、惟大慧语录一帙而已。尝致书道谦禅师曰:“向蒙妙喜开示:从前记持文字,心识计较,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话时时提撕。愿投一语,警所不逮。”谦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无疑之地,后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两段;把这一念提撕狗子话头,不要商量,不要穿凿,不要去知见,不要强承当。”熹于言下有省。有斋居诵经诗曰:“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云云。
以上引分灯录,可知周程等人“最初所亲近者皆属直指宗师”亦可知其“一向在义路上著脚,绝未曾真参力究”也。
且见宗家法法头头指归向上;因此、纵看经教,亦作宗意解会,谓佛法但止如此而已。而因果罪福之实事实理,亦皆以指归向上之意见领会,遂致瞒昧自心,拨无因果,攘人之物以为家宝;拾佛法之遗余,扶儒教之门墙。又恐后生高推释氏,因巧设方法,作盗铃计,横造谤议,陈其祸害,关闭后生,永不能出。又恐或不死心,遂现身说法,谓:吾昔求道,亦曾旁及释老,然皆了无所得,后反求于六经而得之,从此、释老之破绽,一一彻见矣!
宋史四二七、程颢传:“……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于斯理者。”
张载传:“……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
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
夫诸子诚意正心,躬行实践,诚足为儒门师表;但以扶持门墙之念过重,致于最宜感佩表彰之处,反掩人之长以为短;以已之得于人者,反谓人不我若;竟使诚意正心,躬行实践,不能圆满完备,彻头彻尾。噫!可哀也已!一乘居士谓其“入室操戈,喧宾夺主”,其言甚确。
居士分灯录下曰:“溓溪开伊洛之传;而考其源,实自佛印、黄龙点破;所著太极图,亦得之东林。至于两程师弟,靡不从禅门中印证。然则、佛氏何负于儒,而儒者乃忍为入室之戈耶?善乎、伊川之言曰:吾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从出哉?知此、可与谈‘儒释一贯’矣。“
然不详陈其故,关裹人,决不肯服。宜将诸子学佛得益处;及以宗意错会教意,因兹不信因果,不信轮迥,不唯悖佛,亦悖儒经处;及自谓求道于释老皆不得,后于六经反得处,详陈而明辩之。则赃证具在,不但闭关者佩服而直下出关;纵诸子复生,亦当任过自责,无从置喙强辩。从兹“慧风扫荡障翳尽,佛日重辉宇宙中”矣!
请参阅:明.沈士荣著《续原教论》二卷,姚广孝著《道余录》一卷,清.彭际清著《一乘决疑论》一卷,等书,可知诸子如何排佛,古人如何辩释,恕不一一。
──文钞一、“与佛学报馆书”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