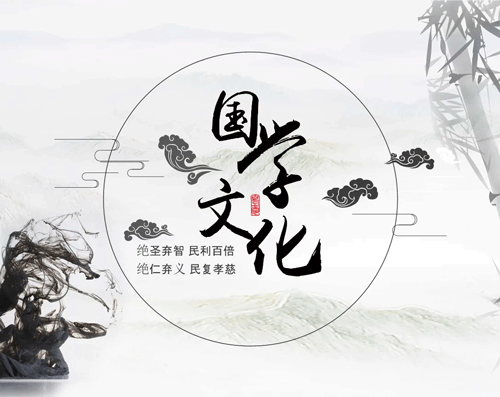会昌灭佛后的湖州唐陀罗尼经幢——兼论武宗灭法对佛教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3-08-04 13:58:16作者:药师网会昌灭佛后的湖州唐陀罗尼经幢——兼论武宗灭法对佛教的影响
严耀中
关于唐武宗的灭佛,史家多有论述,然就会昌法难后所存的陀罗尼经幢观之,似乎乃可进一步探讨与反思。这对我们了解当时中央政令在地方上的执行程度,以及佛教在中国社会的生存能力,甚至是思考政治权力如何处置宗教势力的利弊,大有裨益。
(一)
会昌灭法的结果,《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所载会昌五年八月制中给了我们一些数字:“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十人收充二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二税户十五万人”。又当时日本僧圆仁以其亲身经历对此作了不少描绘和批评,如“三、四年以来,天下州县准敕条流僧尼,还俗已尽。又天下毁拆佛堂、兰若、寺舍已尽。又天下焚烧经像、僧服罄尽。又天下剥佛身上金已毕。天下打碎铜铁佛,称斤两收检讫。天下州县收纳寺家钱物、庄园,收家人奴婢已讫”[1]。而于佛教史颇有影响的宋僧赞宁则认为会昌灭佛是释教东传以来最大的灾难:“从汉至唐,凡经数厄,钟厄爰甚,莫甚武宗焉”[2]。这些都给后世的佛教史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说会昌法难“毁法至酷烈”[3]、“沉重地打击了佛教”[4]等等,仿佛中国佛教由此走向衰败。
然而从遗存的唐代陀罗尼经幢来看,情况又似乎不仅是如此。经幢,即刻经的石幢,在湖州所存的多刻的是陀罗尼经,故称为陀罗尼经幢,或全称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这类经幢直至清代乃有不少保留,湖州是保有地之一。据钱大昕所见录,仅湖州府城天宁寺一地陀罗尼经幢就有十座之多。其云:
“湖州府天宁寺石幢,竹垞先生仅见其八。予尝属沈学士咸熙尽拓其文见诒,较竹垞所得又益其二。今着其目:一为会昌元年十一月胡季良书,后题幢主姚仲文等造。一为会昌三年十月僧令洪书,大中元年十一月重建,后列湖州刺史令狐绹等名。一为大中二年八月曹巨川书,后题湖州刺史苏特名。一为大中十一年四月凌渭书,后列功德主王用为亡妣沈氏夫人建;其一亦凌渭书,年月并同,而所书者乃大佛顶首楞严经也。一为咸通十年六月冯卯书。一为咸通十一年三月建,不见书人姓名,后列军事押衙陈珏等名。一为乾符五年p月立,后题弟子范信为亡妻韩氏卅二娘子建,亦无书人姓名。又二幢皆不见年月,一为周德书,后题徐师范及母王氏名:其一残缺,有处士胡季良姓名,疑即季良书也。诸幢皆书尊胜陀罗尼经,唯凌渭第二幢乃大佛顶首楞严经。曹巨川所书乃六种真言,竹垞概以尊胜经题之,亦未核” [5]。
其实当时湖州府范围内所存陀罗尼经幢远不止此数。据周学浚《同治湖州府志》卷五十所列,存于天宁寺的陀罗尼经幢除以上钱氏所述外,还有五座。一为咸通四年七月仰君儒为亡考妣所立。一为乾符六年四月芮文琛所建。其余三座俱无年月,一为沈颢并母亲杨氏及弟锜、锷等建;一为陈志与妻朱十娘、弟栾直共立;一为范阳汤夫所建。当然,除天宁寺外湖州的其他寺院也存有不少陀罗尼经幢,如当时龙兴寺有中和四年八月沈绶、史章等立的经幢。祗园寺有大中五年正月重建沉宏、沈斌书的经幢二通,及施昱为亡考立的无年月经幢一座[6]。等等。这些足见陀罗尼经幢在该区域内分布的密度。
从以上所引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陀罗尼经幢是会昌五年之前建立的。其中除祗园寺的沉宏、沈斌所书二座经幢标明系“唐会昌五年废毁,大中五年正月二十一日重建立”外,其余虽经历了法难,但多数完好无损。祗园寺经幢还表明经刻如在法难中受到损坏,记文是会于以说明的。这告诉我们所谓“诸道天下佛堂院等,不知其数,天下尊胜石幢、僧墓塔等,有敕皆令毁拆” [7]的记载还是颇有折扣可打的。江浙一带会昌五年前所立的陀罗尼经幢是很多的,从阮元《两浙金石志》等着录中可见不少。因此湖州存有的陀罗尼经幢不是孤立的现象。其实不光是经幢,诸如龙门、云岗石窟中那样众多雄伟的佛教雕像不也是基本完美地保留下来了么?
在湖州,经历法难而得到保留的不仅是陀罗尼经幢,有的还是整个佛寺。宋淡钥所修《嘉泰吴兴志》是现存关于湖州地区的最早方志之一。从其卷十三“乌程县寺院”条中可看出当地一些寺庙在会昌灭佛中废或不废的情况。如,
无为寺:晋王衍舍宅建,唐时士人冯伦、沈演复建,移郡城兴国寺废额榜之。会昌中废。咸通三年又建。本朝治平二年改今额。
开化院:晋永泰元年孙德宗舍宅建。唐会昌五年废。钱氏重建,号菩提寺,当周广顺三年。本朝治平二年改开化院。
瑶山院:唐初郡有通遥寺,废。会昌三年请额建此。咸通二年改今额。
鹿苑寺:梁大同元年处士夏份舍宅建,后废。唐大历间僧明哲募缘请重建,诏赐名永兴寺,元和五年乡贡进士吴行周有记,颜公篆额,即颜真卿也。本朝治平二年改今名。龙兴元年僧元募缘重修。
精舍禅院:陈永定中青州刺史管聚舍宅为院。唐大中元年改为禅院。
上述五座寺院兴废,淡志所记俱详。可见有的寺会昌五年毁了,毁则一定有记载,没有记载的则说明没有被毁过。如精舍禅院至清时还有“陈朝观音、商仲容书额、山门高百尺,谓之三绝” [8],亦可作该寺院未曾毁过之证。该志其他各县情况略同。假若范围更大的话,则此类例子更多。如山阴县天衣寺至宋时还“有(晋高僧)翼公所顶戴,紫坛十二面观音及梁(昭)明太子统遗举(志)公金缕木兰袈裟、红银澡瓶、红琉璃钵,至今具在。又有金铜维卫佛像,本西城(域)阿育王所铸,浮海而至,梁武以施山中,仪相甚伟,今奉于西序” [9]。如此多六朝遗物在该寺完好地保存着,表明该寺在会昌中亦未被毁过[10]。还如宋时分水县有“石佛在玉瑞寺,长不盈尺,刻石为之。旧传陈时所造。寺于邓源别为石佛庵,并貌陈主奉之” [11]。陈朝几个皇帝的崇佛并不亚于梁武帝[12],其被佛教供奉也在情理之中。然此种供奉所体现的连续性,至少说明会昌灭法并没有对它产生什么大的妨害。由此可见当时除了明文规定“上州以上合行香州,各留寺一所”[13]外,各地还多多少少地保留着一些寺院。
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其一是因为会昌五年的灭法虽然看上去来势凶猛,但时间并不长。据《通鉴》卷二四八,祠部上奏废寺毁佛在会昌五年五月,而来年三月武宗薨,宣宗即位,停止废佛。其间不过十个月光景,肯定有许多事来不及做或做不彻底,尤其是石幢、石塔、石像之类,要毁坏它们也并不容易,故多有保存。其二是唐世到了武宗时代,中央朝廷的权威大不如前。藩镇割据,政令不一,对皇帝旨令阳奉阴违、疏漫简怠者当为数不少。突出的如“黄河已北镇、幽、魏、路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佛寺,不条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敕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 [14]。这种情况恐怕其他地方也有。《太平广记》卷一0四引《纪闻》‘李虚\’条云:“唐开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功德移入侧近佛寺,堂大者,皆令封闭。……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虚嗜酒倔强,行事违戾,方醉而州符至,乃限三日报。虚见大怒,便约胥正,界内毁拆者死。于是一界并全。”此事后,李虚未曾受责,更主要的是佛寺由此“一界并全”。这还是号称盛唐的开元中事。至武宗世,天高皇帝远的现象当然更为严重。何况当时文人官吏中崇佛信佛者数目不少,故对朝廷敕令阳奉阴违者必大有人在,否则难以说明为什么会昌法难前所建的佛教寺塔碑像等乃大量遗传后世。一种深殖于社会的宗教是难以被单纯的行政力量所摧毁的。即便象文化大革命那样彻底的破“四旧”(文革还是一场思想运动),也有未毁的寺院佛像。如笔者在文革后期上安徽九华山,目睹半山以下的寺院都毁了,而半山以上的寺庙则大半未毁,佛像乃在。可见古今一也。
湖州的佛教寺院和陀罗尼经幢带给我们另一个信息是,会昌法难虽然对释教来说犹如遭受一场暴风骤雨,但雨过天晴,恢复很快,并非象有的学者所说:“会昌以后,佛教残破”;“佛教经此打击,断断非一百几十年所能恢复” [15] ,“几使佛教绝迹于中国” [16]。在上述湖州唐陀罗尼经幢中约有半数是在武宗灭佛后所建,便是一大证明。不仅是石经幢,就是以土木结构为主的寺院虽在会昌期间受到相当的破坏(如上文所述,不是全部),但会昌之后便得到迅速恢复,“(唐宣宗)大中初,天下寺刹中兴” [17],“天下废寺基各敕重建,大兴梵刹”[18]。典型的如临安治平寺“自会昌中废,大中复兴。更唐末五代至皇朝且数百年,岿然尝为邑里信人所依”,并由此得出“恶念人能以一念使与灰烬散灭,及其复也,有信心者亦以一念能使荒秽瓦砾之区化为梵释之宫、狮子之座”[19]。又《旧唐书》卷十八载孙樵大中五年六月上书云:“陛下即位已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真所谓“齐朝立兰若,曾废会昌初;佛法灭不得,僧徒还居此”[20] 。
在如此迅猛的复教浪潮中,以湖州所在的吴越地区尤甚。据阿部肇一的估计:“(五代时)推断在台州可有一千六百六十三寺,在宁波该是五百九十,那么吴越地方的总数将是八千九十五间寺院。……在吴越方面的寺院数,保守的估计也在数千间之谱”[21]。我们无法对阿部先生的数字作进一步的核审,但包括《湖州府志》在内的江南各地方志告诉我们,其所载唐宋间寺庙之多,足以超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景象。
(二)
皆被称为“三宝”之一的佛经和僧尼是佛教的主要载体,它们的状况决定着佛教的命运。石刻的佛经,如湖州陀罗尼经幢和北京房山石经,如前所述是不易被破坏的。纸质的佛经在会昌法难中虽然会受到相当的损失,但总有不少佛经被一些虔诚的佛教徒所偷偷地保存下来。如僧藏奂“时内典焚毁,梵夹煨烬,手缉散落,实为《大藏》”[22]。 再如《宋高僧传》卷七《唐五台山华严寺志远传附元堪传》云:
“及武宗澄汰之际,禀师先旨,哀恸累夕,以其章疏文句,秘之屋壁。及宣宗再阐释门,重茸旧居,取其教部,置之影堂,六时经行俨然。前置《法华妙经》积字传唱,《摩诃止观》久而敷扬。”
更主要的是佛经主体《大藏经》避过了法难。“会昌废佛以后,唐朝的皇家官藏仍保持着废佛前的形态:以《贞元录》为依据,但陆陆续续有所增补” [23]。此藏及另一部保存下来的《开元录》在晚唐、五代、北宋被屡屡更造,使得佛教的法源滔滔不绝。宋代以后,很多属于传统文化的经史子集都失传了,与此相比,由会昌灭法所造成的佛经失传,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至于僧人在法难虽然遭到冲击,大批被迫还俗,但其中不少人实际上仍是穿着俗衣的僧徒。此类事迹在《宋高僧传》中甚多,兹举数例如下。卷十二《唐长沙石霜山庆诸传附洪諲传》云其:
“俄而会昌中例遭黜退,众人悲泣者、惋叹者,諲晏如也。……时于长沙遇信士罗晏,召居家供施。盖諲执白衣比丘法,初无差失,涉于二载,若门宾焉。大中初,除灭法之律,乃复厥仪,还故乡西峰院”。
同卷《唐杭州龙泉院文喜传》云其:
“属会昌澄汰,变素服,内秘之心无改。遇大中初年例重忏度,于盐官齐丰寺讲说”。
卷十七《唐京兆福寿寺玄畅传》云其:
“会昌废教矣。时京城法侣颇甚傍徨,两街僧录、辩章,同推畅为首,上表论谏。遂着《历代帝王录》,奏而弗听。由是例从俗服,宁弛道情,龙蛇伏蛰而待时,玉石同焚而莫救。殆夫武皇厌代,宣宗在天,坏户重开,炎岗息炽。畅于大中中,凡遇诞辰,入内谈论,即赐紫袈裟,充内外临坛大德”。
这些僧人的宗教意志都十分坚决。如“武宗六年,扬州海陵县还俗僧义本且死,托其弟言:‘我死必为我剃须发,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 [24]。还俗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暂时改换一下外面装束而已,一旦有机会来临,就会立即再穿僧衣。《唐会要》卷四十八“寺”部云:
“大中元年闰三月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为政之源。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会昌五年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如此诏下,还俗的僧人们当然更会闻风而复籍。如僧日照“属会昌武宗毁教,照深入岩窟,饭栗饮流而延喘息。大中宣宗重兴佛法,率徒六十许人还就昂头山旧基,构舍宇” [25]。 再如释神建“贞元八年示寂,其徒以肉身就加塑饰,生气宛然。武宗会昌中汰天下浮屠教,诸僧遂移其身小帆山,出佛洞中。宋元符、崇宁朝两赐师号,为□虚大圣,遇水旱祷辄应”[26]等等。
大中时代的复教浪潮如此猛烈,“恐数年之间天下二十七万髡如故矣”。僧尼总数不会低于会昌之前。其数目之多甚至使当时宰臣们担心,“虑士庶等物力不逮,扰人生事” [27]。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会昌灭佛使大批僧人还俗,本意是让他们回复为农业劳动力,并“递归本贯,充入色役” [28]。但这些僧人多已久离农业劳动。他们不愿意,且在短时间内也不习惯,有的甚至无法(如没有土地)参加农业生产。于是造成如此情况:“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着,无物可吃,艰穷至甚,冻饿不彻,便入乡村劫夺人物,触处甚多,州县捉获者,皆是还俗僧” [29]。因此法禁一开,他们便争先恐后地纷纷回复旧业了。
其二,由于会昌灭法“最主要的原因在经济方面” [30]。在此之前,虽有韩愈上《谏迎佛骨表》,对佛教进行猛烈的攻击。然“而以其纯为文人,率乏理论上之建设,不能推陈出新,取佛教势力而代之也” [31]。“总观韩愈辟佛的言论,纯从效用上观察,不从思想上立论,所以非常肤浅” [32]。此会昌灭佛的发动,是几乎没有思想意识动员为准备的,尤其是在社会基层的群众之中。它只是对佛教的外在形态进行了冲击,而丝毫动摇不了佛教徒们的思想信仰,如一块会昌五年所立的墓志铭中声称墓主“奉释仰道,虽缁衣黄冠,不能嘉也”[33]。此等即所谓“形仪虽变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 [34],灭佛只能激起他们的反感。《太平广记》卷一一六引《传神录》有这样一个说“唐武宗”的故事:
“唐会昌六年,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周穆王)陵下,闻人语于林间,意其盗也,因匿于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而来,朱衣执版,宣曰:‘冢尉何在?’二吏出曰:‘在位。\’因曰:‘录西海君使者何时当至?’吏曰:‘计程十八日方来。\’朱衣曰:‘何稽?’对曰:‘李某(武宗名)坐毁圣教,减一记算,当与西海君同日录其魂。’忽有贾客铃声自东来,朱衣与二吏俱不复见。后数月,帝果晏驾。”
这类传说在当时颇为流行。还如说有一个叫王义逸的“值武宗斥毁佛刹,义逸以家财易诸瓦木,取其精者。”后来“脑发痈,三日而卒。”并通过他的口说出:“君归为我告其家,速毁邸第,以归佛寺,不可辄留” [35]。这些传闻的流播,不仅反映了当时佛教徒们的情绪,其结果更会坚定他们卫护佛教的信念。前文所举的例子都说明了僧徒们身在俗界心在佛,一旦禁令松弛,更不用说是宣宗下诏复教了,便会重操旧业。
其三,大中年间一度还俗的僧众们重披袈裟、复兴佛业是在民间得到相当多的同情,尤其是受到一部分士大夫的支持。这种支持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如“大中初,天下寺刹中兴,(僧清)观入京,请大钟归寺鸣击,并重悬敕额,则集贤院学士柳公权书题也。柳复有《诗序》,送其东归。复请《藏经》归寺” [36]。又如在大中三年“通议大夫前守曹州刺史上柱国清河崔耿撰”的《唐故朝散大夫守陕州大都督府左司马上柱国上谷寇公墓志铭并序》中说寇家“有女子子三人,长奉释氏为比丘尼”[37],似乎是值得称道的。另大中四年“承奉郎前行沂州承县尉上柱国陈圆撰”的《唐故天平军节度使随军将仕郎试左内率府兵曹参军李府君墓志铭并序》中,也盛称墓主“外叼释教,内究典坟;滋味道业,乐在孤寂”[38]。他们都是道地的士大夫。毫无疑问,这些同情和支持加速了还俗僧复业与佛寺重建的速度。
鉴于上述的因素,会昌灭法在迫使僧众返农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也完全失败了。何况正式下令禁佛灭法的时间不到一年,也就是说那些被迫还俗的僧尼离开寺庙的日子还很短,更由于不少僧徒在还俗时乃“执白衣比丘法”,所以僧众作为传法的载体并不因这短暂的法难而受到较大的影响。
综合上面对僧、经、寺庙碑幢在会昌灭佛中的遭遇的分析,可见武宗灭法对于佛教的打击并没有一些僧史描绘得那么大,甚至可以说反而刺激了佛教的发展。从会昌法难到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当中虽然经受了另外一次的挫折,即周世宗的灭法,但佛教发展更甚于前。当时仅江南僧尼人数就达人(其中僧人,尼61239人)[39],几乎为武宗灭佛前的一倍,所谓“天禧承平,合僧尼几四十万,闽浙占籍过半焉” [40]。对此王夫之感慨地说:“(会昌灭佛后)然不数年而浮屠转盛,于是所谓黄檗者出,而教外别传之邪说充塞天下,禁之乃以激之而使兴,故曰难也” [41]。法难,对佛教来说真可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三)
会昌灭法在近世学术界引起重视的,还因为是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它成了佛教各宗兴衰的一个关键,促成了禅宗的发达和其他宗的没落。如胡适先生云:“(会昌灭佛)尽管残忍而又野蛮,但对禅僧不但危害不大,相反的,可能倒加强了他们的势力,因为他们根本无须依靠庞大的财产和堂皇的建筑。实在的,他们甚至对于经典也不必依赖”[42]。周叔迦先生云:“会昌灭法,经籍全被焚毁,丧亡殆尽,各宗一时顿衰,唯有禅宗不籍经教,不立文字,更得到发展,于是先后有五家之成立[43]”。在所谓衰落的诸宗中,说是以密宗为甚。如仁同先生云:“(会昌法难)后,所谓瑜伽(即密宗)者,但有法事而流为市井歌呗”[44]。
然此种说法有失片面。因为佛教诸宗的兴衰主要在于其内因,在于其思想仪规是否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短暂的政治打击仅是很次要的因素。就拿禅宗来说,它之发展主要在于它的中国特色最明显,此各家早有所论。何况禅宗在会昌前已成汹涌之势,诚如印顺法师所言:“禅宗到了唐初,忽然隆盛起来” [45]。禅宗在唐宋以降显得比较兴旺,除了其他的原因外,天台、华严诸宗都在广义的范围内奉行禅道,也在客观上有力地壮大了禅的声势。天台、华严等宗在唐以后乃有其兴盛期,此处暂且不论,即使是密宗,会昌之后照样兴旺不衰,湖州那批唐陀罗尼经幢就有力地证明这一点。那些经幢表明当时密宗乃风行于民间。如唐咸通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所立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建立幢主”是“乡贡进士赵匡符”。他誓“念火轮金刚真言一万五千遍,念佛顶尊胜陀罗尼一万六千遍,念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一万三千遍,……念龙树菩萨化身一切法陀罗尼五万遍,念天王心真言十万遍,念欢喜咒十万遍,念天厨陀罗尼三万遍,右匡符所念前件经咒及舍钱建立此幢” [46]。一个乡贡进士在数量上能念那么多经咒,即使有所夸大,也突出地反映了密宗在当时民间的普及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经幢的刻石题名情况来看,它包含着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不仅有僧尼和一般的男女信徒,而且有“专勾当军事押衙陈剔,衙前虞侯吴允中”,“湖州乌程县丞陆恪”“当州军事衙前散将沈颢”等一大批州县要吏,更还有“中大夫使持节湖州诸军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国彭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令狐绹”,“大中大夫使持节湖州诸军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国苏特” [47]这样地方高级主官。尤其是令狐绹,当时是宰相之子,自己后来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辅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册拜司空。……为太子太保,分司东都” [48],系一代权贵。这证明密宗在当时不止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也有着强大的政治后援。武宗的灭佛并没有使它在这二方面受到什么显着的损害。如何看待北宋以后密宗传受系统的消衰,此非本文讨论的范围[49],本文在上面仅要指出的是会昌灭法与它并无多大干系。
密宗如此,其他宗的情况更是若此。说它们的兴衰被武宗灭法所左右,是缺乏足够证据的。当然,包括会昌法难在内的所谓“三武一宗”的灭佛对佛教有着不小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在于从政治及经济上对整个佛教的限制,使其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不能成为一种与封建政体相对抗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由于这几个皇帝没有,在当时也不可能用思想意识的力量来铲除佛教,因此佛法不仅没有被灭掉,反而刺激了它的传播。这就是湖州唐代陀罗尼经幢给我们的信息。
--------------------------------------------------------------------------------
[1]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
[2] 《宋高僧传》卷十七《护法总论》,第435页。
[3]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一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页。
[4] 吕征《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九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2页。
[5]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五“湖州府天宁寺石幢”条,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362页。
[6] 周学浚《同治湖州府志》卷四十六至五十四。其中还列举湖州府内各地所存陀罗尼经幢多座。
[7]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第178页。
[8] 《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七“归安县精舍寺”条。精舍禅院为精舍寺之前身。
[9] 施宿等纂《嘉泰会稽志》卷七,“山阴县天衣寺”条。
[10] 该《志》与《嘉泰吴兴志》一样,寺曾被毁则一定有记。如同上书同卷“山阴县秘云寺”条:“大同十年将军毛宝舍宅建,会昌毁,大中五年重建。”
[11] 郑遥等纂《景定严州续志》卷九,“分水县古迹”。
[12] 参见拙文《陈朝崇佛与般若三论之复兴》,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四期。
[13] 《唐会要》卷四十八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99页。
[14]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第196页。
[15] 分见东初《隋唐时代的佛教》、罗时宪《唐五代之法难与中国佛教》,均载《中国佛教史论集(二)――隋唐五代篇》,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版第57、188页。
[16] 龙慧《略述中国佛教的教难》,载《中国佛教通史论述》,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第190页。
[17] 《宋高僧传》卷二十《唐天台山国清寺清观传》,第527页。
[18] 同上书卷六《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第190页。
[19] 见潜说友修《咸淳临安志》卷八十四“治平寺”条。
[20] 《嘉泰吴兴志》卷十三“德清县三德院”条引岑硕诗。
[21] 阿部肇一《中国禅宗史》,中译本,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249页。
[22] 《宋高僧传》卷十二《唐明州栖心寺藏奂传》,第276页。
[23] 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第三章,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24]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9页。
[25] 《宋高僧传》卷十二《唐衡山昂头峰日照传》,第274页。
[26] 胡崇伦修,马章玉增修《康熙仪真县志》卷九《神建传》。
[27] 《唐会要》卷四十八“大中五年七月宰臣奏”,第1000页。
[28]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第180页。
[29]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第195页。
[30] 《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九章,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74页。
[31] 《隋唐佛教史稿》第一章,第40页。
[32] 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第五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33] 见《唐故河中府永乐县丞韦府君妻陇西李夫人墓志铭并叙》,载《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1页。
[34] 《续补高僧传》卷六《唐龟洋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35] 《太平广记》卷一一六引《传记附录》“王义逸”条。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21页。
[36] 《宋高僧传》卷二十《唐天台山国清寺清观传》,第527页。
[37] 文载《唐代墓志汇编》第2273、2274页。
[38] 文载《唐代墓志汇编》第2277页。
[39] 《宋会要辑稿》第二百册“道释一”,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875页。
[40] 徐硕修《至元嘉禾志》卷二十六《崇福田记》。
[4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37页。
[42] 胡适《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和方法》,载《胡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43] 《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2页。
[44] 仁同《中国佛教大乘八宗》,载《佛教各宗比较研究》,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45] 印顺《中国禅宗史》,台中广益书局1971年版第232页。
[46] 《同治湖州府志》卷五十“金石略五”。
[47] 《同治湖州府志》卷五十“金石略五”。
[48] 《新唐书》卷一六六《令狐楚附子绹传》。
[49] 密宗在宋以后流传的情况,可参见拙着《汉传密教》第三、四章,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