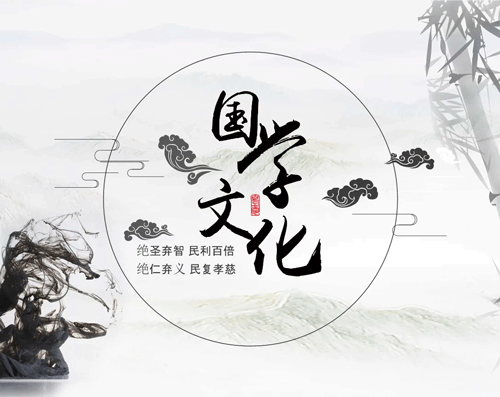瑜伽中道论——欧阳竟无佛学思想申论
发布时间:2023-08-15 14:46:49作者:药师网瑜伽中道论——欧阳竟无佛学思想申论
肖永明
近现代以来,随着欧阳竟无等佛学大师的提倡阐扬,唯识独成一学,逸出所有宗派,呈一时之盛,影响及于佛教内外,甚至连整个社会思潮的深处也多多少少地受到了影响。然而,其间虽经欧阳竟无、太虚、吕澂、熊十力、王恩洋、唐大圆等人抉择料简、往还论辩,但在近现代乃至当代的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大环境中,本来就名相纷繁、义理艰深的唯识学,就仍然容易使学人触处生碍、随类执解而无法贯通了。今发意再作抉择料简、方便条贯,以期使此唯识一学不再局于一隅,而能入归佛教缘起中道法海,进而易于契入佛法道妙!
当然,我们的思考还得从欧阳大师的抉择开始。
欧阳竟无在归投杨仁山居士门下学佛之后,专精深研瑜伽行一派、法相唯识一宗、唯识一学所宗经论,却发现自来归为一派一宗一学的法相唯识,应该分为法相与唯识二宗。他在1916年写成的第一种法相诸论叙——《百法五蕴论叙》中就说:“约缘起理建立唯识宗,以根本摄后得,以唯有识为观行,以四寻思为入道。约缘生理建立法相宗,以后得摄根本,以如幻有诠教相,以六善巧为入道。”(1) 在1917年撰成的《瑜伽师地论叙》中,欧阳竟无又反复说明此义,他说:“唯识义者:众生执我,蕴、处、界三,方便解救,遂执法实,心外有境;救以二空,又复恶取;是故唯言遣心外有境,识言遣破有执之空,而存破空执之有,具此二义,立唯识宗。……法相义者:世尊于第三时,说显了相,无上无容,则有遍计施设性、依他分别性、圆成实性。复有五法:相、名、分别、正智、如如。论师据此,立非有非空中道义教,名法相宗。”(2) 直至1938年,欧阳竟无在与支那内学院院友讲谈论义中,还是再三致意法相与唯识分宗之说,他说:“盖弥勒学者,发挥法相与唯识二事也。初但法相,后创唯识。弥勒《瑜伽》中谈法相于《本事分》,而谈唯识于《抉择分》。是法平等曰法相,万法统一曰唯识。二事可相摄而不可相淆,亦复不可相乱,此弥勒学也。……所以唯识法相必分为二者,世尊义如是也。世尊于《楞伽》、《密严》,既立五法、三自性之法相矣,而又立八识、二无我之唯识理。”(3) 可见,法相、唯识分为二宗之义,是欧阳竟无佛学思想中始终一贯之说,其于此间殷勤反复再三致意,而对唯识学也有精研的章太炎也以之为“独步千祀”之论,这确实是令我们深思的。
在欧阳竟无对法相、唯识分宗之义的反复阐释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法相与唯识之间有两点基本差别,那就是,一,法相是约缘生理而立,而唯识则是约缘起理而立;二,法相义在万法平等,而唯识义则在万法统一。但是,在法相与唯识之间又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法相、唯识都证成佛法中道义教。关于法相义之五法、三自性,欧阳竟无已明确指出,“论师据此,立非有非空中道义教”,而关于唯识义,欧阳所谓“是故唯言遣心外有境,识言遣破有执之空,而存破空执之有,具此二义,立唯识宗”,其义也即《成唯识论》所谓“我、法非有,空、识非无,离有离无,故契中道”。(4)
但是,欧阳对法相唯识之二异一同的抉择,又是安隐于名相纷繁之中,并不容易索解体认领会。何以法相唯识二异能成一同,一同却有二异?欧阳之以十义等理证成,其阐释不可谓不复杂,自然令人索解繁难。所以,我们很有必要由欧阳之抉择返溯原典,作一方便条贯。
那么,从什么地方开始我们的返溯呢?
“毕竟,现实中我们所具有的唯一直接经验就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意识。”(5) 并且,西哲笛卡尔所找到的我们存在的基点也是,“我思故我在”,那么,我们的思考就应该从这种最直接、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入手,看看我思与我在这种经验事实在佛教中又是怎样被阐述呈现的。
对此,佛早有断言,佛说,“我说识所缘,唯识所现故”。(6) 识所缘,唯识所现,但识所缘又是什么呢?
《解深密经》说:“‘世尊!若诸有情自性而住,缘色等心所行影像,彼与此心亦无异耶?’\‘善男子!亦无有异!而诸愚夫由颠倒觉,于诸影像,不能如实知唯是识,作颠倒解?’” (7) 可见,所谓识所缘,是指缘“色等心所行影像”。而所谓影像,又称影像尘,就是人们所见所闻所缘之境界相状。但是,“心识并不能象镜子映物一样,直接映现境相,必须由感觉器官(五根)接受外境信息(五尘),由外界信息与感觉机制的共同作用,在自心中变起一个‘影像尘\’,心识对此影像尘进行分别,才形成对境相的现量。影像尘是心识直接分别的对象,相对于外缘本质尘名‘疏所缘缘\’而言,叫做‘亲所缘缘\’。《宗镜录》卷五五释影像尘云:‘影者流类义,像者相似义,即所变相分是本质之流类,又与本质相似,故名影像’。影像,即是影子和画像,虽然依本质而有,相似于认识对象,但既经根识之变现,便非认识对象本质尘之实体,也非全同于本质尘的原样,是一个常有主观性的东西。” (8) 然而,相对于影像尘,本质尘又称为本质法尘,并且一般而言,所谓境相,是只指称影像尘,而并不兼及本质法尘的,所以,可以说,识所缘,唯影像尘,唯境相,唯相,而相只是唯识所现耳!
当然,“根境识三缘和合而变起一个带主观性的影像尘这件事,可谓世间的第一奇事,其中的机关奥妙,非轻易而可弄明白。”(9) 因为,人们总是习惯性认为所见所闻境相是实有的、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形成于现代之初的传统物理学中的宇宙是一架巨大的永不停息的机器,由不可毁灭的物质粒子构成,由不可毁灭的能量驱动,由永恒不变的数学法则控制。”(10) 但是,即使是实证性的、还原式的现代科学,随着其发展,也已经认识到了,“人肉眼所见的不同颜色,其实体其实是波长不等的光波的电磁震荡;人耳所听到的各种声音,其实体其实是声波在空气中的辐射。……科学还发现了人不能感知的X光、红外线、紫外线、超声、次声等的实有,发现在宇宙电磁光谱中,人肉眼可见的光带,只是其中很小的一段,还有大段的不可见光存在;在宇宙声波中,人耳能听到的频率,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段,还有大段不可闻的超声波、次声波存在。”(11) 所以,人们所见所闻所缘的境相,也可以说,人们可见可闻可缘的境相其实都离不开人们的主观感觉意识,都是随人们的主观感觉意识变现出来的。
然而,人们所见所闻所缘为什么只是见其可见闻其可闻缘其可缘之影像尘,却不见不闻不缘其不可见不可闻不可亲缘之本质法尘呢?这要从识缘相层面寻出其中奥妙,其实是不可能的。这就像要了解电视图像如何形成的原理一样。“让我们假设有一个聪颖且求知欲很强的人,但他对电学或电磁辐射一无所知。他第一次看电视时,他也许会认为电视机里真的装着小人,因为他在屏幕上看到了他们的图像。但当他察看电视机内部,发现里面只有些线路、电容器和晶体管等物时,他也许会作更深层的假想,认为图像或许是由于电视机各部分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当他发现,部件移动时,图像会扭曲或消失,部件归于原位时,图像又恢复正常,他的上述假设看上去就更加真实可信了。人们提示他,图像其实是依靠机器接收到的远方的无形的影响才产生的,他也许会认为那是不必要的和蒙昧主义的,并予以驳斥。当他发现电视在开机和关机时机器的重量相等时,就更增加了外物不可能进入机体的信念。他承认,他无法详细解释图像是如何通过机件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但他也许会称,从原则上讲,是可能做出这样一种解释的,其实,通过大量的深入研究,最终是可以找到答案的。”(12) 事实上,电视机屏幕上的图像,并不是由电视机体里的电线、电容器、晶体管等部件产生的,而是接受了外界发射的电视信号而变现出来的,电视机体也只是起了一个接受信号并将之变现为图像的作用。识缘相而变现出影像尘,也可以如此比譬了知。识之了别境相而成影像尘,只不过是依心法转变生成的。心之于识,法之于相,是可以说为识相缘起依据的。
当然,在佛教经论中,心识法相却往往是通称不分的,似乎并没有作这样明确的简别。但是,正如《成唯识论》引述《解深密经》言“所缘唯识所现”及《楞伽经》言“诸法皆不离心” (13) 来作为成立唯识的理据一样,我们其实也可以依之作进一步的方便简别,即,依“所缘唯识所现”立相唯识,而依“诸法皆不离心”立法唯心。
如此方便施设,也是于理决定的。
那么,所谓心,所谓法,其理云何?

依佛教经论解之,《俱舍论》说“集起故名心”,而《解深密经》,则谓“色声香味触等积集滋长故”,“名为心”,并且此之所谓心,《解深密经》说为阿赖耶识之异名,总称为一切种子心识。但《解深密经》也只是将阿赖耶识说为“亦名为心”,却并没有将眼耳鼻舌身意识亦称为心,于此可见,阿赖耶识作为识之总持才可以通于心。(14) 比譬而言,阿赖耶识如电视机信号接口,而心则如信号接口所接收的信号。就其直接关联而言,信号接口与信号是谐合的,而心与阿赖耶识也是相即的,所以,阿赖耶识亦可名为心。但是,相对于眼耳鼻舌身意识之各别了别,集起之心必然只相对于总持眼耳鼻舌身意识之阿赖耶识,却是不能对应于眼耳鼻舌身意之各个分识的,这也就是《解深密经》言“由此识(阿赖耶识)色声香味触等积集滋长故”“亦名为心”的缘故。
所以说,与眼耳鼻舌身意识乃至阿赖耶识之作为有情众生之感性经验事实不一样,作为眼耳鼻舌身意识之所缘的色声香味触法积集滋长的心,是不能说为具有识之各别了别乃至总持的现实感性经验事实的。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相对于识来说,心是形而上的。
这里,让我们了解一下关于梦的情形,就可以更容易地了解心与识的关系。“当我们做梦之时,梦中的一切似乎都极其真实。当我们醒来时,我们会认识到那实际上是一场梦。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因果律似乎有所不同。在睡梦中,一个事件可能似乎是另外事件的原因,如此等等。但对于醒来的自我来说,显然,‘我,做梦者’才是那个梦(包括事件、相互关系和其他一切)的原因。……设想一下一个人从物质世界的‘梦想\’中清醒过来,于是因果律就与我们想的(和我们被传授的)不同:‘我,做梦者’(或‘我们,集体的做梦者’)是事件和关系的原因。意识之外的集体的/普遍的‘心\’是个人的‘心\’的经验世界的创造者。”(15) 所以,从梦的情形我们也可以推知,与所谓客观的物质世界只不过是梦中的经验世界,而导致梦中物质经验世界产生的却是“我,做梦者”之梦心一样,识缘相之变现境相影像尘,也是以阿赖耶识亦名为心之心为依据的。
当然,“此梦境非即是心,梦去心不异,故不一;当梦之时,离此梦境亦无别心,故不异。是故梦境举体即心,而相状万般,心举体成梦而自性不改。” (16) 所以,识与心也可说是不一不异,今言其异,方便施设,便于索解而已,并且,特标心异于识之感性经验之可感可执之不可感不可执实耳。心有异于识之经验现实可感,那么,由心变生之法当然也就有异于相之所谓客观实在可知了。
在人们看来,我们所见所闻所缘的境相,从根本上讲,当然都是客观实在的。所谓山河大地、草木虫鱼,似乎都是真真实实的,其实,这些都不过是识之遍计所执而已。所以,佛教又“依相立法”,立义于依他起相上破除遍计所执相而入于圆成实相之平等真如法尔。《解深密经》说:“诸法相略有三种。何等为三?一者,遍计所执相;二者,依他起相;三者,圆成实相。云何诸法遍计所执相?谓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别,乃至为令随起言说。云何诸法依他起相?谓一切法缘生自性,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谓无明缘行,乃至招集纯大苦蕴。云何诸法圆成实相?谓一切法平等真如。于此真如,诸菩萨众勇猛精进为因缘故,如理作意,无倒思惟为因缘故,乃能通达。于此通达,渐渐修习,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方证圆满。” (17) 所谓遍计所执相,只是于一切法上“假名安立自性差别”,并不如法,而所谓依他起相,则是一切法之缘生自性,已显缘生之相,也并不体现法住法位之法。只有圆成实相平等真如,如如法尔。所以,依相所立之法,也只有“于彼依他起上,常远离前遍计所执,二空所显真如为性” (18) 之圆成实相才能显示如如之法。
所以,所谓法之以“任持自性轨生物解”之“轨持”为义,也只有在圆成实相上才能依相成立。也就是说,决定物质现象变现的本质只有在破除了各种虚妄偏执以后才能呈现。当然,能够呈现这种物质现象之本质,即佛法所谓影像尘之依托的本质法尘的,也只有超越了为分别局限了的识之羁绊的心才有可能。
可以说,“每个人的‘心\’都不是相分离的(尽管每个人的大脑看上去是相分离的);它们在某种层面上下意识地产生联系。物质世界对于较大的‘心\’与梦想对于个人的‘心\’有着相似之处。从根本上讲,我们不是通过有形的感官,而是通过深层直觉才触及到现实。” (19) 因为,我们有形的感官意识所感觉意识到的物质世界,就象梦之幻现事物一样,其实是并不真实的,那么,对于感觉世界中的人,真正能触及到真现实,也就只有通过深层直觉了。也许只有通过深层直觉才能突破感觉意识世界的局限,进而进入到不再是因每个人而相分离的真正的“心理状态”之中。在这种心理状态中体认的真现实,与感觉世界中的物质世界,当然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法之与相也就应该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了。
但法之究为何物?我们不一定能以“深层直觉”去现量证知,而佛菩萨之圣言量却早已说得明白。《杂阿含经》一开经便说:“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当观色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观。正观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如是比丘心解脱者,若欲自证,则能自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如观无常,苦、空、非我,亦复如是。”(20) 佛已明言,当观色等法为无常。如是观法无常、苦、空、非我,则心解脱。反之,如果也象识缘相而执为有实,执为有常、有我、非苦、非空一样,又执法为有实,执为有常、有我、非苦、非空,那么,心也就被识之虚妄分别习气所染所拘,不得解脱。所以,法应被观为无常、苦、空、非我。
那么,法为什么其实也只能被观为无常、苦、空、非我呢?龙树菩萨说得直截,他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即中道义”。
当然,瑜伽行法相唯识义理也认为,“境界相在心识上的现起,乃是一个缘起法,有着多方的缘起依据。……可以明确地讲,心识所现境界,并非只是由于自内心识,而是还有外缘依据的。……境界相既有内心识的能变缘依,也有外界待变缘依,那么‘法\’这一词,在唯识学体系里的含义就不是单一的,它至少有两层含义,两层所指。第一是指心识所现境界,即是专门指对心识内所现之相的。第二则是指境界的如实缘依,即是专门指对使境界相现出的诸内外缘——由于心法(内缘)可以别立而说,所以‘法\’的如实缘依尤指外缘。这两层含义,是有根本区别的,绝不可混淆,否则会引起种种混乱和误会。世俗所说的‘法\’,其实是指心识内境相,妄执此境相为实际外在,不了其为心内幻现,所以这时说‘法\’,是在第一层意义内转,是单就其相而说的世俗有。若从胜义谛上了知境相其实是内外诸缘所成,于心内所现,并非实际外有,没有实境,但有诸缘,这时候说‘法\’,便不指境相而转指诸缘,是在第二层意义上转,是就真如缘依而说的胜义谛。第一层含义是相分、见分,第二层含义则是现相的诸缘依之实际如如。缘非是相,离世俗一切不实妄想,称为如如,如如成相,相非如如,‘法\’究竟指如如还是指相,必须严格区别,方不生混乱。”(21)其实,既然“‘法\’的如实缘依尤指外缘”,而“世俗所说的‘法\’,其实是指心识内境相”,“是单就其相而说的世俗有”,那么,将这种意义上所说的“法”,直接指称为“相”,就更如实而不致产生歧义,而“法”则可以专指识所变现境界相的外在缘依——本质法尘。但是,我们也不能将此作为外在缘依的法就径直“指诸缘”,否则又会引起另一层次上的混乱。
因为,“佛法的根本要旨,是‘缘起性空\’,众缘相待,众缘相成,凡有自性似现之法,其自性皆是众缘所成,只是假有,故说之为性空。但是这个缘起法,必待表示,能表之法,即是众生心识。心识住于缘起海中,自己亦必是缘起法,方能表此缘起法海。所谓心识表法,即是心识因外缘变带而内现境相,‘表\’即是‘现\’。所以讲缘起有两种,一是即心相而说的缘起,表为境相与及名言的俗有缘起。这时,若执相为实在外有之法,说因说缘,皆妄认实外,便落生灭有无等见,成生灭因缘,为世俗戏论。若知相非外在实有而只是自心现,此时说因说缘,则成圣教假立顺世俗之方便,是为俗谛。二是离心相而住,不待名相表示的如如之缘起,是为胜义谛。缘起如如,离言绝相,非生灭法,不可破坏,内缘外缘,平等而住。”(22) 既然自性似现之法只是众缘所成,而如如之众缘则是“离心相而住,不待名相表示的”,那么,所谓如如之缘起,就可以说是离心法而住的另一层面,在这一层面上,既是“缘起如如,离言绝相,非生灭法,不可破坏,内缘外缘,平等而住”,不待心识法相表示的,但同时,即此缘起故性空,而且即性空故缘起。缘起故性空,性空故缘起,不待识缘相、心缘法然后变现也,则能表之识心,其识性、心性也当即空性。但也必须经由识现相、心生法然后才能入于空性。此中次第,也不可杂蹋。
识缘相而变现影像尘,但影像尘又是有外在缘依——本质尘的,必须根尘识三缘和合然后方成,所以,识缘相只能说是识现相,却是不能说为识生相的,因为尚有外在缘依——本质尘的缘故。然而,相对于识缘相之为现,心缘法却可以说之为生,因为所谓心,“色声香味触”等法“积集滋长故”,说“名为心”,所以,所谓“法有必待心缘,缘有必待心现”之“心现”因“滋长”故,应该说之为生,即法有则心生,反之,心生则法有,因此,也可说为“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其实,“法有必待心缘,缘有必待心现”之与“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无非是说明,与识缘相之变现之有能变所变、能现所现之相对依持转换不同,心缘法其实是庶几乎能所同时、主客不分的。因为,“诸法皆不离心”,心外无法,法外也无心,不似识亲缘影像尘之相外尚且有疏缘本质尘之法。
当然,识缘相之现又是以心缘法之生为依的,而其所依又都是依于缘的。只不过约缘生理则可说之为识现相,也即欧阳竟无所谓“法相义”,而约缘起理则可说之为心生法,也即欧阳竟无所谓“唯识义”。所以,所谓识缘相,所谓心缘法,都不过是一种因缘和合的方式而已,只是相对而言,识缘相而变现我们现实世界之林林总总,是我们亲切所见所闻的,而心缘法所生的种种理解,也是我们可以推知的,但是真正的因缘和合本身却并非就是识缘相而现,心缘法而生这些变现生灭的方式,真正的因缘和合,却是不生不灭,离言绝相的。这种因缘和合是当体即与空性不二的,是缘起当体即性空,而非待缘起生灭以后而谓之空。所以,真正意义上只能说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里是不一不二、相异相成、相即相契于中道的,是毕竟无所谓能所主客分别的。
所以,真正的因缘之义,是属于第一义之胜义谛,是非生灭的,也非变现的,当然也就是不可言说的。但是,不言说则众生无由证悟,又得方便言说,所以,就有了种种方便施设之法门。由心缘法层面则可立唯心教义,由识缘相层面则可立唯识教义,但在成立唯心、唯识教义的同时,又必须时时回向本际,不离中道的。然而,佛法流传过程中,方便设教之时,又总难免出现各种偏执之流弊。说唯心,则不知法唯心而相并不唯心,沦为唯意志主义,终至与山河大地、草木虫鱼并不唯心生灭之世间极成道理相违,当然也就不易使此世间众生起信;说唯识,则又不知相唯识而法并不唯识,沦为唯物质主义,终至与人之有不为形役的形而上精神超越的心性体证相违,当然也是不易使此世间众生信同的。而在这两种偏失中,尤以第一种偏失最为严重。这主要是因为佛教总体上是以追求精神超越为特征的,于是更容易使人误会佛法之义只在唯心所造而已,而无法随顺融会提升世间法。由此不仅对整个佛教会产生这种误会,就是对唯识一学,也容易产生唯心的误解。
正是基于对误唯识一学为唯心之论的倾向的敏锐而深刻的洞察,欧阳竟无才汲汲于将法相唯识分为两宗。
欧阳竟无《唯识抉择谈》抉择杂以唯识义理以谈唯心之论为与分别论者“心性本净,客尘所染”相似之谈,其体用混淆,次第错乱。他说:“分别论者无法尔种,心性本净,离烦恼时即体清净为无漏因,如乳变酪,乳有酪性,是则以体为用。体性既淆,用性亦失(体为其因,因是生义,岂是不生?自不能立,须待他体以为其因,故用性失。)”(23)说心性本净,则不立法尔种,即不知如如缘起,不生不灭而真如自真如,无明自无明;说客尘烦恼所染,却不立烦恼自烦恼之有漏因,即不知烦恼染相唯识变现,同虚妄性,并不能与心性等质的。这样,本属心法层面之义,却与如如缘起及虚妄唯识上下牵带,杂置一处,自然是质碍难通了。次第错乱,自然进而就有“真如受熏缘起万法之说,遂至颠倒支离,莫辨所以,吁可哀也!”(24)
当然,欧阳竟无还是在唯识学狭义范围内来抉择此义的,所以他强调将法相与唯识分为二宗。其实,他只不过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在唯识学的层面上,将法相连带一并与唯识分开,将法相归为缘生层面,而将唯识归为缘起层面。其实,进一步探究,由唯识一学上溯法相唯识一宗再上溯瑜伽行一派终至根本佛法义趣,其深义甚深义则应该是将相唯识归于缘生一面,而将法唯心归于缘起一面,并且,其要义还在于,无论欧阳竟无所谓的法相义、唯识义,还是此中所谓相唯识、法唯心,它们分属缘生与缘起之最终义趣却又是一致的,那就是,相唯识之“法相义”之以缘生为依,法唯心之“唯识义”之以缘起为依,皆以如如因缘为最终依归。并且,识与相相异而相应,心与法相异而相应,识与心相异而相应,相与法相异而相应,识现相与心生法相异而相应,识现相与缘生相异而相应,心生法与缘起相异而相应,识现相与心生法相异而相应而相异相应于缘生与缘起相异而相应于如如缘依。既然都最终依归相应于如如缘依,也就自然与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法则相契,相契相应于中道义教,远离增减边执,于此方可云瑜伽相应中道义教,而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名相分别,方便施设,严别狭义,广义融通,则必须随义而安,而对于学人而言,这才又是最最重要的。
注释
1 欧阳竟无《百法五蕴论叙》,《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欧阳渐、吕澂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页。
2欧阳竟无《瑜伽师地论叙》,王雷泉编《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194页。
3欧阳竟无《辨唯识法相》,《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第94页。
4玄奘糅译《成唯识论》,林国良《成唯识论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页。
5哈曼《后现代的异端:作为原因的意识》,《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6《解深密经》,演培法师《解深密经语体释》,天华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13页。
7《解深密经语体释》,第317页。
8陈兵《真实论》,《法音》1993年第7期第7—8页。
9同上,第8页。
(10)鲁珀特?谢尔德拉克《作为习性的自然法则:科学的后现代基础》,《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01页。
(11)陈兵《真实论》,同上,第8—9页。
(12)鲁珀特?谢尔德拉克《作为习性的自然法则:科学的后现代基础》,同上,第106页。
(13)参见《成唯识论直解》第507页。
(14)参见《解深密经·心意识相品》
(15)哈曼《后现代的异端:作为原因的意识》,同上,第157页。
(16)吴可为《辨“真如”义——略论核心思想》,《法音》1998年第7期第11页。
(17)《解深密经语体释》,第167—168页。
(18)《成唯识论直解》第607—608页。
(19)哈曼《后现代的异端:作为原因的意识》,同上,第156页。
(20)《大正藏》第二卷第1页。
(21)周永西《‘心现\’与‘心生\’之辨析》,《灵山海会》2003年秋,总第9期,第46页。
(22)同上,第48页。
(23)《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第42页。
(24)同上,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