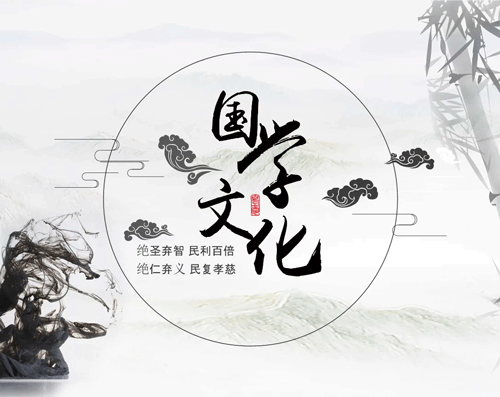玄高从学佛陀跋陀罗的一桩公案
发布时间:2023-09-05 12:16:03作者:药师网玄高(402-444)是否从学佛陀跋陀罗(359-429),是中国禅学史上的一桩著名的疑案,近日宣方博士发表了《南北朝禅学史上的一桩疑案——玄高从浮陀跋陀学禅说辨伪》(《中国文化》1998年春夏卷)一文,重提是说,以为其乃讹传。是故有重加检讨的必要。
此案之所以有疑,主要是由于时间问题。《高僧传?玄高传》谓:“闻关中有浮陀跋陀禅师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师之,旬日之中妙通禅法。跋陀叹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于是卑颜推逊,不受师礼。”然据《祐录》,佛陀跋陀罗于义熙七年(411)离开长安,因此玄高从学之时最多只有十岁,似乎不大可能。
对于这一问题,有些学者怀疑浮陀跋陀另有其人,有些学者认为僧传所记年龄有误。徐文明在博士论文中提出了将玄高生年提前十年的方案,即改为公元392年(徐文明博士论文《中土前期禅学思想研究》第二章第三节),这样一来,倒是消解了玄高年龄过小的矛盾,只是根据不足。虽然僧传有玄高受戒(受具足戒一般是在二十岁以后)以后闻浮陀跋陀在关中弘法之说,但仅此为据显然是不够的。僧传记玄高之母于弘始二年(400)感梦受胎,弘始三年(401)二月八日生高,轻易改动这一记载是不严肃的。又据《高僧传?慧览传》,慧览“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东大明中(457-464)卒,如此他生于公元397至404年,既云二人年少时齐名,则其年龄相若,故僧传云玄高生于弘始三年是有根据的。
那么玄高于十岁时从学觉贤是否有可能呢?据僧传,玄高十二岁时始辞亲出家。十岁之时尚未入道,更谈不上受戒习禅。那么是不是如宣方博士所说,这是一个后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呢?其实不然,因为慧皎在《禅论》中明确说道:“沙门智严躬履西域,请罽宾禅师佛驮跋陀更传禅业东土,玄高、玄绍等并亲受仪则。”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就不应轻易否定这一结论。
觉贤离开长安的时间其实未必是在义熙七年,也有可能是在义熙九年或更迟。义熙七年说有三种资料为证,其一是僧祐《出三藏记集》觉贤传,这是最早的材料,也是此说的始作俑者,其二为《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其三为《法显传》。
僧祐谓觉贤被摈之后,先至庐山,“自夏迄冬,译出禅数诸经”,后“以义熙八年,遂适荆州”,如此可以推断觉贤是在义熙七年初离开长安的。僧祐还记录了一个故事,觉贤既至荆州,“时陈郡袁豹为宋武帝太尉长史,在荆州。佛贤将弟子慧观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饱辞退,豹曰:‘似未足,且复小留。’佛贤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设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饭,饭果尽。豹大惭。既而问慧观曰:‘此沙门何如人?’观答曰:‘德量高邈,非凡人所测。’豹深叹异,以启太尉。太尉请与相见,甚崇敬之,资供备至。俄而太慰还都,请与俱归,安止道场寺。”
僧传所述与此大同,只是加了一句“宋武南讨刘毅,随府界于江陵”。据《宋书》,刘裕以义熙八年九月讨伐刘毅,十月王镇恶克江陵。袁豹既为太尉长史,故随到江陵。如此觉贤当在义熙八年十月以后到达江陵,其到豹府乞食,当在此年末或次年初。刘裕还都是在义熙九年二月,觉贤亦当于此时同归建康。
这一故事与史实无违,袁豹其时确为太尉长史,且正在江陵。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可靠证据,即《法显传》。现存本《法显传》有“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之句,而文未又有“是岁甲寅”,表明此传作于义熙十年,这就足以证明觉贤义熙十年前就已经到了京都。
如此似乎觉贤义熙七年离长安,义熙九年到建康已经成了定案。然而,《高僧传?慧观传》却提出了另一说法:“什亡后,乃南适荆州。州将司马休之甚相敬重,于彼立高悝寺,使夫荆楚之民去邪归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与观相遇,倾心待接,依然若旧。因敕与西中郎游,即文帝也。俄而还京,止道场寺。”
按照此说,则觉贤与慧观等还都是在义熙十一年(415)八月。那么义熙七年离开长安说还能否成立呢?司马休之于义熙八年九月取代刘毅任荆州刺史,但其真正进驻江陵须在十月收复之后,而其获得任事之权怕是应在义熙九年二月刘裕还京以后。因此觉贤与慧观可能是在义熙九年或十年离开庐山的,其离开长安当在义熙七年以后。这也只是出于推测,更为重要的是“什亡后”一句提供了线索,表明觉贤与慧观是在罗什卒后离开长安的,因此罗什卒年的确定对于确定觉贤离开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罗什的卒年恰恰是一个难解之谜。僧祐未言罗什的具体卒年,但说是在义熙中。到慧皎的时代,就已经弄不清了。《高僧传》罗列了弘始七年(405)、八年(406)、十一年(409)八月二十日三种说法,但倾向于最后一种说法。这些说法一直流行到唐初,吉藏(549-623)仍然采用弘始七年十二月或弘始八年八月二十日说(吉藏《百论疏》卷上之上[大正藏42册,235页下],《法华游意》[大正藏34册,649页下]),表明他也没有新发现。然而,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三却收录了僧肇所撰的《鸠摩罗什法师诔》,其中明确提到罗什“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薨于大寺”,即在弘始十五年(413)。
僧肇的诔文应当是最为可靠的资料,但由于发现较晚,是故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怀疑。首先对此表示怀疑的是塚本善隆,他的理由无非是前人如梁代的僧祐、宝唱、慧皎,隋代的费长房等皆不知此诔文的存在,然而这一理由显然是不足为据的,因为前人未知、后世有新的发现之事并不罕见。鎌田茂雄也是依照这一思路提出疑问的。他指出,隋代的吉藏亦未见此诔文,更为重要的是,撰述《开元释教录》的智昇亦未引用此诔文,而《开元录》中明明提到道宣的《广弘明集》,假如僧肇的诔文果然收入此书的二十三卷,那么智昇为什么不加引述呢?因此鎌茂雄认为此诔文是作于公元七三○至七九九年间的伪作(鎌田茂雄《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224页,关世谦译,佛光出版社1986年版)。既然僧肇诔文为伪作,那么罗什的卒年还是应以僧传为准。
这一论据显然是不充分的。智昇未加引用,并不表明道宣的《广弘明集》未收,说智昇未看到也缺乏说服力,或许是他对诔文的真实性也有一定的怀疑,因为道宣未说明其出处,隔了这么久才出现,今人不加深信,古人当然也会抱有疑问。
认定诔文为伪作必须有适当的理由,作伪的第一前提必须是对作伪者有好处,否则他又何必如此呢?那么伪作这一诔文又有什么意义呢?鎌田茂雄所谓“盖或许为了显示权威而说僧肇作《肇论》的年代,罗什依然在世,且受其教化”(同上)未免过于牵强。按照这一说法,三论宗应当最有理由编造诔文,然而在公元八世纪,三论宗早就已经传承不明了。
证明罗什在弘始十一年后去世有多种证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见于《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的《成实论记》:
“大秦弘始十三年,岁在豕韦,九月八日,尚书令姚显请出此论,至来年九月十五日讫。外国法师鸠摩罗耆婆手执胡本,口自传译,昙晷笔受。”
由此可知,至少弘始十四年(412)的九月罗什仍然在世,足以破除弘始七年、八年或十一年说。鎌田茂雄却认为它不可靠,证据是“译者及译出年时的记载过于简略。虽有尚书令姚显其名,但在清万斯同的《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弘始十三年的姚显是卫大将军,不是尚书令;弘始十三年及十四年的尚书令是姚弼,因此《成实论记》的记载,应不足采信”(《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229页)。
此记依僧祐之说只是出论后记,简略一些亦无足怪。弘始十三年姚显固然不是尚书令,但姚显做过尚书令却是无疑的。僧叡《自在王经后序》有“秦大将军、尚书令、常山公姚显,真怀简到,彻悟转诣”之句,此序作于弘始九年,表明其年姚显已经是尚书令了。《弘明集》卷十一收录了《道恒道标二法师答秦主姚略劝罢道书并姚主书》,其中也有“今敕尚书令显”之语。这都表明姚显做过尚书令。虽然弘始十三年时姚兴以子弼为尚书令、大将军,姚显被降为卫大将军,但《后记》作者以姚显曾任过的最高职务尚书令名之,也不为过,若谓其时姚显不再是尚书令,故不可以尚书令名之,那就是胶柱鼓瑟了。
依《成实论记》,《成实论》应当是罗什最后译著之一。鎌田茂雄却千方百计证明《成实论》的早出,举《高僧传?昙影传》为证,其有“初出《成实论》,凡诤论问答,皆次第往返。影恨其支离,乃结为五番,竟以呈什,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后出《妙法莲华经》……”之句,鎌便认定先出《成实》,后出《法华》,其实这只是僧传笔法,不足为据。《僧叡传》谓“什所翻经,叡并参正。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译经至此,乃言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叡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突然。’其领悟标出皆此类也。后出《成实论》,令叡讲之”,是不是也可证明《成实论》出在《法华》之后呢?
鎌田茂雄又引《历代三宝记》卷八“《成实论》二十卷或十六卷,弘始八年出,昙略笔受,见二秦录”,说明其早出,然他自己也不相信托名僧叡的《二秦录》,其实此说可能并非毫地根据,只是弘始八年当作义熙八年(412),因为《成实论》译讫是在义熙八年九月十五日。托名僧叡的《二秦录》可能是南人之作,用的是晋之正朔,后人不明底细,当成了弘始八年。
《成实论》之晚出还有其他证据。僧叡为罗什门下第一人,撰诸经序,多兼述此前译出的其他经论,在现存的诸经论序中,无一语道及《成实论》,这足以证明其出也晚。据吉藏《三论玄义》、《中论序疏》、《中观论疏》等,僧叡作过《成实论序》,并为讲论之始。《三论玄义》卷上云:“昔罗什法师翻《成实论》竟,命僧叡讲之。什师殁后,叡公录其遗言,制论序:‘《成实论》者,佛灭度后八百九十年,罽宾小乘学者之匠,鸠摩罗陀上足弟子诃梨跋摩之所造也。其论云:色、香、味、触实也,地、水、火、风假也。精巧有余,明实不足,推而究之,小乘内之实耳。比于大乘,虽复龙烛之于萤耀,未足喻其悬矣。’”《成实论序》是在罗什卒后作的,并且表达了罗什本人的意图,这是否表明《成实论》为罗什最后译著之一,僧叡在其生前忙于讲解,未及为序呢?
僧叡《成实论序》很可能有此论翻译的时间,但是由于吉藏坚信罗什卒于弘始七年或八年,对于这一时间不肯采纳,未引全序,也使后人丧失了可以确定此论译时和罗什卒年的最可靠的资料。《中观论疏》一末还有“叡师《成实论序》,述罗什语云:‘马鸣是三百五十年出,龙树是五百三十年出’”之语,表明此序总结了罗什所译大小乘经论,在诸序中最为珍贵,可惜不见全豹。
《成实论记》其实是不必怀疑的。若谓其不足采信,那么就等于认定为伪作。那么伪作此记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伪作者又有什么好处呢?
《成实论记》可以辅证诔文的可靠性,但诔文所持的“四一三说”并非只此一证。
据《高僧传?昙邕传》,慧远弟子昙邕充当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信使,“为远入关致书罗什,凡为使命十有余年”,任继愈等以为“罗什死于公元413年,此首次投书约在403年,为东晋元兴二年”(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613页注(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其实没必要如此反推。慧远致罗什的第一封信有“去岁接姚左军书”之句,罗什以弘始三年(401)十二月二十日至长安,时已岁末,就算左将军姚嵩马上致书慧远,慧远接到此信之时也应在弘始四年之初了,一个“去岁”就足以表明慧远最早是在弘始五年(403)首次致书罗什的。昙邕原为武将出身,故能“强悍果敢”,不辱使命。其于弘始五年首充信使,且为使命十余年,则罗什必当于弘始十五年(413)以后卒。
汤用彤据以史书,认为刘裕讨平桓玄(公元404年)之后遣大参军诣姚显通知,姚显使吉默报之,至是两国通好,交聘不绝,“约在此时前后(义熙元年顷[公元405年])慧远得姚左军书”(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253页)如果慧远于义熙元年得姚嵩之书,那么他首次致书罗什必在义熙二年,如此则昙邕为使“十有余年”就到了义熙十二年,未免太迟。那么姚左军是否另有其人呢?后秦崇佛最剧者除姚兴、姚泓父子外,当首推大将军、常山公姚显与安成候姚嵩二人,姚兴钦慧远之德风,赠以龟兹国细缕杂变像,又令姚嵩献其珠像,可见姚嵩与慧远是有交情的。故此“姚左军”当为姚嵩无异。据僧肇《百论序》,弘始六年(404)译《百论》时姚嵩为秦司隶校尉、安成候,未有左将军之衔,僧叡《法华经后序》则称秦司隶校尉、左将军、安成候姚嵩,则姚嵩当于弘始六年至八年间加左将军衔。据诸经序,罗什于弘始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译出《大品》,又加校正,至弘始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讫。同年十月十七日罗什又与弗若多罗共译《十诵》,是《百论》之译出,当在此年四月至十月间。姚嵩或以是年末加左将军,并致书慧远,告以罗什入关之事亦未可知。若然则慧运首次致书在弘始七年,昙邕为使则至弘始十七年(415)。因为按照情理,姚嵩通报罗什入关之讯,不应太迟。
僧叡《喻疑》(一说作者为慧叡,误)有“及至苻并龟兹,三王来朝,持法之宗,亦并与经俱集。究摩罗法师至自龟兹,持律三藏集自罽宾,禅师徒众寻亦并集关中。洋洋十数年中,当是大法后兴之盛也”之语,所谓大法兴盛“洋洋十数年”,足以破除弘始十一年说。此“十数年”是以罗什为核心的,罗什以弘始三年末到长安,以弘始十五年终于大寺,正好满足十数年。罗什卒后,觉贤被摈,卑摩罗叉出游关左,佛陀耶舍辞还外国,大师星散,长安佛教已呈衰败之势,与兴盛无缘。因此若谓罗什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去世,则其弘法时间只有八年,此后诸大师亦多散去,长安佛教盛极而衰,何来佛法兴盛“洋洋十数年”之说?
僧肇有《答刘遗民书),鎌田茂雄认为此书作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299页),汤用彤则认为是弘始十二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33页)。这一时间的确定与道生离开长安的时间有关。《出三藏记集》道生本传谓其于义熙五年(409)还都,由于途中在庐山稍事停留,故谓其于弘始十年(408)离开长安,其年夏末到达庐山比较合适。刘遗民看到了由道生带来的《般若无知论》,对其中一些说法有疑问,故而于次年十二月致书僧肇,僧肇的回信应当在第三年的八月。将道生离开长安的时间定为弘始九年(407),无非是为了证明罗什卒于弘始十一年说能够成立,其实这里面仍有不少问题。道生在罗什门下号为“四圣”之一,其从学罗什的时间不应太短,道生约于弘始六年(404)与慧叡、慧严、慧观等自庐山到达长安,若谓九年夏便离开,未免过短。道生有《维摩经注》,且僧传有“初关中僧肇始注维摩,世咸玩味,生乃更发深旨,显扬新异,及诸经义疏,世皆宝焉”之句,故而生注是在肇注流行之后,其离开长安不应过早。即便此书果作于弘始十一年八月十五日,若罗什五日之后便当辞世,僧肇还说什么“什师休胜”、“什师于大寺出新至诸经,法藏渊旷,日有异闻”,恐怕与事实及情理不合吧。假如罗什果如鎌田茂雄一再试图证明的那样是患急症而亡(无非是为了弥补与肇书的裂缝),那么五日前还在“出新至诸经”(当是支法领携至)的罗什必定有未完成的译作,而僧传本传却谓罗什临终自述“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烦,存其本旨,必无差失,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焚身之身,舌不焦烂”,可见并无未曾译完的经典,《十诵》业已完成,只是罗什还想加以删治而已,今既不果删烦,“存其本旨”,亦无差失。罗什对自己的译作是充满信心的,认为自己留下的都是经得住考验的佳作,于此并无遗憾。

僧肇《答刘遗民书》本身就说明了其写作时间。《出三藏记集》卷三将僧肇《长阿含序》与《答刘遗民书》并列以说明《四分律》的译事。所谓“三藏法师于中寺出律,本末精悉,若睹初制”,按照肇序,指的是弘始十二至十四年佛陀耶舍于中寺出《四分律》,这就证明《答刘遗民书》必然作于弘始十二年以后。而此时罗什还颇“休胜”,正忙于译经,怎么会于上年就去世了呢?
僧肇《上奏主姚兴表》中有“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之句,《开元释教录》以此来证明罗什卒年不可能在弘始十一年,因为如此则最多八年,不满十年,不得谓“十余年”,《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亦以此来印证弘始十五年说,似乎都忽视了僧肇曾至姑臧从学罗什的传说。《高僧传?僧肇传》有“后罗什至姑臧,肇自远从之,什嗟赏无极。及什适长安,肇亦随返”之语,然而这一传说唯见于僧传,不见他籍印证。在现有僧肇著述中,看不出这一传说的证据。如果此说属实,则僧肇为罗什奏地第一位弟子,而僧叡在《大品经序》中提到参与译经的义业沙门慧恭、僧 、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叡、道恢、道标、道恒、道悰等,没有提到僧肇的名字,或谓前述皆是宿旧,僧肇年少,不预其列亦无足怪。然佛门并不只是强调年腊,入门先后也很重要,若是僧肇早在姑臧就从学于罗什,算是罗什关中弟子第一人,而且其时已到了“名震关辅”的冠年,僧叡也不好不加提及吧。
据史传,虽然姚苌父子早就“挹其高名,虚心要请”,然“诸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入”,姚兴不得已,于弘始三年五月派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大破隆军,隆只好于九月上表归降,并乖乖地交出罗什。因此僧肇若是在此之前西至姑臧,吕隆未必会接纳他,不将他当作秦国奸细就不错了。吕光父子并不弘法,故虽然罗什“停凉积年”,却是“蕴其深解,无所宣化”,也就是说,罗什在凉十八年,根本没有从事弘化,并无弟子,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敌国的僧肇能否远至是个问题,即便能穿越关卡,恐怕也无计停留。因此所谓僧肇远至姑臧从学罗什数年是不合情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后世似乎也无人认可僧肇远至姑臧求学的传说。吉藏《百论序疏》谓僧肇“罗什至京师,因从请业”。吉藏以僧肇为“玄宗之始”,又搜罗极广,对僧肇最有研究,他的意见是应当重视的。元康《肇论疏)卷下谓“在什公门下十有余载,十九事什公,三十一亡,十余年也”,僧肇十九岁时即弘始四年(402),也就是说,罗什至长安后才从学,与吉藏之说一致。吉藏《百论疏》又云“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亦云十有二年”,而自弘始三年末至弘始十五年四月正好为十二年,恰好证明罗什的卒年为弘始十五年。此说亦为元康《肇论疏》所本,僧肇晚罗什一年而卒,罗什卒时他三十岁,十九岁从学,故在罗什门下正好十二年。若认定罗什于弘始十一年卒,则其时僧肇只有二十六岁,从学罗什也只有八年,不可谓十余年,因此元康也是认定罗什先僧肇一年(弘始十五年)而卒。
因此所谓僧肇至姑臧从学罗什说是慧皎取自传闻,并不可靠。自弘始十一年向前反推十二年以确定僧肇从学罗什的时间是不足取的。《上秦主姚兴表》称“肇以微躯,猥蒙国恩,得闲居学肆.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虽众经殊趣,胜致非一,涅槃一义,常以听习为先”,这段话如何断句非常关键,若谓至“得闲居学肆’为一句,则“十有余年”有可能从姑臧算起,然细推文意,颇觉不然。此表处处推崇姚兴,肇之闲居学肆固是蒙受国恩,其得以在什公门下十有余年,何尝不是出自国恩!若谓自姑臧算起,又与下文不符。罗什在姑臧时处境尴尬,与弄臣一般,吕氏根本不允许他讲经说法,是以十数年中,毫无作为,所谓众经殊趣、涅槃胜至,僧肇是无缘听习的。因此无论僧肇是否到过姑臧,此“十有余年”都只能从罗什至长安后算起.弘始十一年说是绝无成立之可能的。
从现有资料来看,实在难以发现诔文有何“不足置信”之处。鎌田茂雄所谓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八记载罗什年龄为“七十四岁”(《中国佛教通史》第二卷229页),也许别有所本,因为从大正藏本实在看不出来这一记载,原文明明是说罗什弟子道融活了七十四岁,根本没提罗什的年龄,据此认定诔文“不足置信”,实在不足置信。诔文言“昔吾一时,曾游仁川。遵其余波,纂承虚玄。用之无穷,钻之弥坚。槃躍日绝尘,思加数年。微情未叙,已随化迁。如可赎兮,贸之以千。时无可待,命无可延。惟身惟人,靡凭靡缘。驰怀罔极,情悲昊天。”一方面表达了僧肇对罗什的深情,一方面又将自己与罗什的师生之情与孔颜相比,也表明了僧肇强烈的自信。作此诔时,僧肇正好三十岁,其才其识,其命其身,正可与颜子相比。僧肇以颜子自期非始于此,《百论序》有“钻仰累年,转不可测”之句,其时僧肇始逾冠年,已经是“名震关铺”、颇怀时誉了。诔文还称“人之寓俗,其途无方。统其群有,纽兹颓纲。顺以四恩,降以慧霜。如彼维摩,迹参城坊。形虽圆应,神冲帝乡。来教虽妙,何足以臧”,这是僧肇对罗什身受妓女、不住僧坊之秽行的辩护。罗什此行是为了统群有、振颓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寓俗无方。“顺四恩”其实特指国主恩,是说罗什身受妓女是出于国主之命,为报其恩,须顺其意;“降慧霜”其实是强调智慧最为重要,以回护罗什戒行之有亏、禅修之不足。更以罗什与维摩相比,倒是极为恰当。“来教虽妙”,也许指的是觉贤,觉贤与罗什一派不合,孤高其行,不修人事,僧肇心服其德,口不肯承,主要是出于情感与宗派之见,不得不为罗什辩解。
因此诔文虽然发现较迟,其可靠性还是不容怀疑的。罗什的卒年亦当以诔文为准,即弘始十五年四月十三日。
既然罗什卒于弘始十五年,那么觉贤就不可能在义熙七年离开长安,也不可能在义熙九年至建康。其实依据史实,觉贤在义熙九年与刘裕一起还都的可能性也很小。刘裕当时恐激诸葛长民为乱,轻舟潜归,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大可能带觉贤师徒同归的。那么又何以说明《法显传》“就禅师出经律”之说呢?
《法显传》之后有一段跋文:
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夏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斋。因讲集之际,重问游历。其人恭顺,言辄依实,由是先所略者,劝令详载。显复具叙始末,自云:“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达万一之冀。”于是感叹斯人,以为古今罕有。自大教东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夫成功业者,岂不由忘失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这段跋文“迎法显道人”一句日本镰仓古抄本作“慧远迎法显道人”,章巽认为此句表明慧远促成法显与觉贤合作译经之事,并非亲迎。郭鹏认为非亲迎之说,似与文章不符,此段跋文或为慧远之作,或为远弟子雷次宗所写(郭鹏:《佛国记注译》148页注(2),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法显来京是否与慧远有关,不得其详,然义熙十二年八月七日慧远入灭,夏末之时,慧远还有没有精力顾及此事是个问题。且加上“慧远”二字,与文法不合。是故此事恐与慧远没有直接关系,亦非雷次宗所为。
从其文意来看,此跋文很可能为慧观之作。因为义熙十二年冬天法显正好在道场寺与觉贤共译《摩诃僧祇律》。慧观为觉贤首徒,也是道场寺务的主持者,由他出面迎请法显是很自然的。这段跋文表明两点,一是义熙十二年夏末法显始到京师,二是《法显传》有详略两个版本。
诸说多谓法显义熙九年至京,是泥于略本之说。略本原作于义熙十年,大概是在刘道怜驻地京口所作。现存本实为后来详载改订之本,成于义熙十二年之后,故加进了“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之句,然略本最后的“是岁甲寅”却未加改动,难怪后人受其迷惑。
此说非只此一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三谓“法显以晋义熙十二年还都,岁在寿星”,此前又引《法显记》说明诸戒本的由来,这表明僧祐是读过《法显记》的,他仍然肯定法显十二年还都,表明是明了“就禅师出经律”之始末的。
从译经之时也可看出这一说法的可靠性。觉贤来京之后,最先翻译的是法显带来的《摩诃僧祇律》,以十二年十一月始,十四年二月讫。如果义熙九年二人都到了京师,为什么拖到三年以后才开始译经呢?依《法显传》,义熙十年时就已经出经律了,那么为何诸录皆谓译事最早始于义熙十二年呢?
是故《法显传》之说事出有因,不足以作为觉贤义熙九年二月还京的证据。觉贤应如慧观本传所述,于义熙十一年八月随刘裕还京,止道场寺。
僧传昙邕本传谓其“凡为使命十有余年”后,“京师道场僧鉴挹其德解,请还扬州”,前述昙邕以弘始七年首次出使,十余年后则至少是弘始十七年,即义熙十一年,其最后一次出使是故应在罗什卒后,其时京师道场寺的住持是僧鉴而非觉贤。这表明觉贤义熙九年还京是不可能的。
觉贤还京的时间可下定论,然其离开长安之时尚难定断,或为弘始十五年末,或为十六年初。罗什以四月十三日卒,四月十六日即开始夏安居,七月十五日结束夏坐,在这段时间内,罗什徒众即便对觉贤有怨言,也不好公然加以驱逐。因此觉贤被摈应当是在弘始十五年秋以后。
慧远《万佛影铭》有“晋义熙八年,岁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台”之说,汤用彤先生认为:
昔慧远奉侍道安,尝闻西域沙门言西域有佛影(按安公曾作《西游志》,盖集录游方僧人传说)。及晋义熙中,在庐山值罽宾禅师佛陀跋多罗(约于六七年顷到庐山),及南国律学道士(不知为何人,但似非法显。因显时尚未归来),详问其所亲见,乃立台画像(义熙八年五月立台),并刻铭于石(义熙九年九月作铭)。孑是挥翰之宾,佥焉同咏(详《广弘明集》慧远《佛影铭》)。并命弟子道秉远至江东,嘱谢灵运制铭,以充刻石(见《广弘明集》。铭作于义熙九年秋冬之后,故言及法显。又铭之序中,言“庐山法师闻风而悦”,乃指远公在远方闻天竺佛教流风遗泽而悦,非闻法显言也。铭中有“承风遗则”句可证。)(《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46页)
其详情也“未晓然”,只是在觉贤等亲睹佛影者来山之后,才具悉其状,始“图而铭焉”。
据远《铭》,图铭之时是在义熙九年九月三日,故立台与画像并非同时。这个细节非常重要,立台之时觉贤未至,图(画像)铭之时始至,故与前说无违。汤先生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一细节,才会得出觉贤早至及南国道士非法显的结论。其实谢灵运《佛影铭》说得非常清楚,这个“南国律学道士”就是法显。谢《铭》谓“法显道人至自祇洹,具说佛影,偏为灵奇,幽岩嵌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庐山法师,闻风而悦。于是随喜幽室,即考空岩,北枕峻岭,南映滮涧。摹拟遗量,寄托青彩”,说得再明确不过了,正是因为听到了法显“具说佛影”,慧远才“闻风而悦”,“图而铭焉”。所谓慧远“闻天竺佛教流风遗泽而悦,非闻法显所言”是站不住脚的,不闻法显之言,慧远何以得知天竺佛教之流风遗则?如果不是指佛影的具体相状,只是普通的流风遗则,慧远早已从他人得之,为何不早加图铭呢?谢《铭》言“曾是望僧,拥诚俟对。承风遗则,旷若有 。敬图遗踪, 凿峻峰”,与前言一致,是谢灵运在编故事了,而谢当时可能并未见过法显,他的消息来源则是慧远弟子道秉。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六谓“(义熙)九年,迦维卫国沙门佛驮跋陀罗至庐山入社”,堪为觉贤九年始至之一证,也可知汤先生强说之失。
法显以义熙八年七月至青州,在彭城住了一冬一夏,其后则至庐山。他的本意,有可能是经庐山到长安,完成译经之弘愿,然在此山遇到觉贤师徒,知长安居之不易,故徘徊不前。觉贤或在此之前到山,故慧远首言之。
由是觉贤离开长安当在弘始十五年七月十五日之后,看来罗什徒众是害怕觉贤成为长安佛教领袖、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的,迫不及待地要赶走他及其门徒。
《出三藏记集》本传谓觉贤至庐山后,“自夏迄冬,译出禅数诸经”,如此则其到达庐山是在八月底,其离开长安应当是在弘始十五年七月。僧传谓觉贤在庐山停留岁许,也就是不满一年,可能他在其年冬天译出禅经之后便西至江陵。
觉贤不东下京师却西至江陵,大概他对慧远解其摈事抱有一定希望,期待受到姚兴及关中僧众的邀请,重回长安。在江陵,觉贤师徒受到司马休之的欢迎,他的天竺五舶来华的预言也得到了证实,是以荆楚之民,归之者众。后休之败逃于秦,觉贤师徒又受到刘裕的尊崇,当时后秦内忧外患,实力大减,觉贤也断绝了重回长安的念头,于其年八月随刘裕东归建康。
觉贤西至江陵,还因罗什卒后,江陵成为新的佛教中心。卑摩罗叉亦在罗什卒后出游关左,在寿春石磵寺弘律,约于义熙十年末或十一年初南适江陵,在辛寺坐夏,开讲十诵,慧观“深括宗旨,记其所制内禁轻重,撰为二卷,送还京师”,京师有谚曰“卑罗鄙语,慧观才录”。这也表明慧观在罗什卒后离开长安是可信的。在觉贤师徒和卑摩罗叉离开江陵后,昙摩耶舍又来到这里,仍住在辛寺,大弘禅法。后来法显亦至江陵,卒于辛寺。可见江陵已成当时的佛教中心。
觉贤既以弘始十六年初离开长安,那么他又是何时始至关中的呢?汤用彤谓贤“约于弘始十二年(公元410年)至长安,当不久即被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18页);法藏《华严经传记》卷一觉贤传谓其“达青州东莱郡,闻鸠摩罗什在长安,欣然而来,则弘始十年四月也”(大正藏51册2073页中);任继愈等谓其约于弘始十年(408)至,411年被摈(《中国佛教史》第三卷14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当依此。吉藏则谓弘始七年(405)至(吉藏:《中论序疏》,《三论玄义》卷上)。究此三说,七年嫌早,十二年过迟,惟十年稍近之。
智严与宝云、法显等同游西域,据《法显传》,法显等约于弘始二年十月到达乌夷国,在此住了两个月,此间智严、宝云等亦至,因为其国人不修礼义,待客甚薄,智严等三人不得已返向高昌,以求行资,从此法显未与智严相见(后来二人又在建康得遇),故在《法显传》中未言智严日后行踪,僧传、《祐录》亦未言智严到达罽宾的时间,然罽宾距西域最近,智严到达的时间应约在弘始四年(402)。智严居此国三年,与觉贤在路上又走了三年,其到达长安应约在弘始九年(407)。所谓弘始七年,当是始发之时。
弘始七年说汤先生似亦赞同,其谓“智严于罽宾从佛大先比丘受禅法三年(约在公元401至 403年),并请佛陀跋多罗相偕东归(至长安应在元兴三年[公元 404年]之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75页),是说智严401年即到罽宾,从学三学即至403年,又三年归则应在405年。汤先生对僧传所载觉贤浮海东还说颇有怀疑,以为此事不见于《智严传》(《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218页),若从陆路东还,则耗时更少(罽宾在北天竺,陆路更近,若南下经六国至交趾,再浮海至青州,自青州至长安,确实是绕了一个大圈子)。然智严是否在弘始三年(401)便至罽宾是个问题,依《法显传),弘始二年(400)末智严返向高昌,其后法显再未提及智严,表明智严一直落在后边,而法显越过葱岭到达邻近罽宾的乌苌国的时间是约弘始四年(402)四月,在此坐夏,法显未到罽宾,只到过与此较近的陀卫国、弗楼沙国,智严到达罽宾的时间不应早于法显、宝云到达罽宾周边诸国之时,因此最早是在弘始四年。既如是,智严从学三年,路途三年,不应皆是刚好满两周年,因此弘始七年至长安是根本不可能的。
任继愈等持弘始十年说,或亦与《肇论》所载之《致刘遗民书》中有“(支法领)请大乘禅师一人,三藏法师一人,毗婆沙师二人”之说有关,《四分律序》谓法领于弘始十年与佛陀耶舍(三藏法师)俱还,则佛陀跋陀罗(大乘禅师)也有可能同至。然觉贤浮海还,必不与法领同行,至于法领在天竺是否也曾邀请过觉贤,就不得而知了。
言觉贤于弘始九年至,还有一个旁证。觉贤未至时,关中众僧咸从罗什学禅,罗什亦猢狲称王,编译禅经,教习禅法,而弘始九年闰月(二月)五日僧叡却“重求检校,惧初受之不审,差之一毫,将有千里之降。详而定之,辄复多有所正,既正且备,无间然矣”(《关中出禅经序》),这大概是由于觉贤既至,僧叡恐见笑于方家,故重求校正。
僧叡《喻疑》称“究摩罗法师至自龟兹,持律三藏集自罽宾,禅师徒众寻亦并集关中”,来自罽宾的持律三藏非指一人,有弗若多罗(弘始六年前至)、卑摩罗叉(弘始八年至)、佛陀耶舍(来时不详)等,佛陀跋陀罗师徒或于卑摩罗叉至后不久即至,故有“寻亦并集”之说。
又慧远二致罗什书有“去月法识道人,闻君欲还本国,情以怅然”之句,或谓此书作于义熙二、三年间(《中日佛教通史》第二卷385页)。此事颇费思量,罗什受姚兴之尊崇,弟子三千,威荣无比,何以有返国之思?莫非觉贤远至,关中乐静之徒咸转事之,不久便有弟子数百,罗什颇有失落之感么!罗什戒行有亏,心怀惭德,弟子亦多修人事,不类僧行,而觉贤一门“邕邕肃肃”,仪范清素,让罗什师弟相形见绌,觉贤弟子是否以此指斥罗什不得而知,便有其事,罗什恐怕也无从辩解。觉贤至后,太子姚泓请至东宫与罗什辩论,罗什未占上风。觉贤未至时,众人咸谓罗什天下莫二,而卑摩罗叉、佛陀耶舍等既为罗什之师,自然不会与之争锋,觉贤一来,罗什在禅律方面很快就落了下风,觉贤对其义学也不敢恭维,这样众人视之若神的罗什颇有光彩尽失之感,他负气欲行就不足为怪了。
觉贤在长安或言住大寺(《智严传》)、或说宫寺(《答刘遗民书》)、或说齐公寺(《出三藏记集》)、或说石羊寺(《玄高传》),其实诸说并不矛盾,因为他乐于游化,未曾定居一寺。
觉贤以弘始十六年初离开长安,其时玄高已经十三岁,完全有可能从学禅法。僧传谓玄高十二岁出家,“至年十五,已为山僧说法,受戒已后专精禅律”,此为一段,下文“闻关中有浮陀跋陀”为另一段,并无玄高受戒之后始至关中之义。玄高十三岁至关中学禅,十五岁正式收徒开法,有弟子百余人,此时乃其隐居麦积山时。玄高乃少年天才,“聪敏生知,学不加思”,故不可以常情视之。
玄高专精禅律,且颇重神通法术,与乃师宗风一致。其徒玄畅南下之后又以三论、华严之学见称于世,表明玄高一门重视禅慧,且觉贤师徒所译诸经,也传到了玄高那里,是以玄畅在北方时对华严经就有精深的研究,故在江东成为第一个疏解讲述华严大部者。
玄高从学觉贤实无可疑,且玄高一门既为定学之宗,又颇重戒智,三学并重,止观双开,使觉贤之学大弘于南北,为后世禅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虽然后来传承不明,其贡献还是不容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