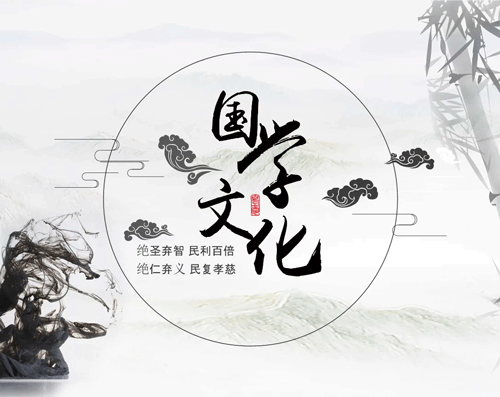佛教社会”如何可能?——中国佛教公共形象的社会建构
发布时间:2023-08-23 11:25:45作者:药师网佛教社会”如何可能?——中国佛教公共形象的社会建构

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李向平
一.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社会变迁,使中国佛教的发展从中获益良多,同时亦使中国佛教的存在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佛教经济的发展、寺庙管理方法的改变、僧人行动模式的丰富、参与社会的积极效果……,已经在具体的社会事实层面,以佛寺为基础,建构了格式与意义不一的佛教格局。比如官寺、商寺、民寺、私寺,或者是修持型、经济型、文化型、园林型,甚至是出现了地域上的分别,如都市佛教、乡村佛教等若干类寺庙模式的建构;与此相应,佛门僧人亦以其宗教行动为依托,分别涌现近代太虚大师所期待的那样,具有不同所长的僧人类型,管理型、修持型、文化活动型、讲经说法型、社会活动型、佛门领袖型 [①] 等等。这些现象,诚然是印证了当代中国佛教的变迁和进步,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中国佛教的运作模式,正面对着功能与结构等层面的多元分化。
如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建设,必须落实到社会建设层面才能对所有的中国人具有普遍意义那样,中国佛教亦应当把佛教的制度建设、道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弘法利生、服务社会的诸项事业再度整合,立足于一个社会建设的层面,把佛教发展视为一个社会系统的整体运作。否则,当代中国佛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就会遭遇瓶颈之限,缺乏更大进步的驱动力。
就当代中国佛教的公共形象而言,此乃佛教内部的道风建设、丛林制度与现代管理制度、佛教之社会关系、佛教与非佛教之间、佛教信徒与非佛教信徒之间、寺庙组织与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既包涵了寺庙、僧众、居士等等层面的关系,同时也包涵了寺庙、僧众、居士与其他宗教组织、宗教信徒、非宗教组织、非信教公民之间的交往关系和交往结构。所以,佛教形象建构的社会学意义,就不仅仅是佛教内部的自我认同,佛教信仰的个人修持,而是社会其他组织、其他社会成员在经与佛教寺庙、佛教信徒交往中,对佛教的一种接纳、一种认同。而这种接纳与认同的拒绝或断裂,就等于宣告了佛教公共形象的失败和堕落。
二.
依据佛教传统而言,庙要像庙,僧要像僧。此乃佛教形象的根本。寺庙与四众,即个人信仰表达、佛寺组织形象的整合,就是佛门形象的总体构成。然其为佛教的自我建构,内部形象。否则,己身不度,何以度人?纵使天花乱坠,也近似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然而,这种佛教公共形象的建构,无不限制在佛教寺庙的架构之中。当年太虚大师孜孜以求的佛教革命之一,就是希望佛教能够走出寺庙,建设教团,在佛教与社会之间建构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中介,从而使中国佛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关系,大致能够专业化、组织化和制度化。因为,佛教寺庙和隶属于佛寺的佛教信徒,它们难为制度化的、固定的社会组织。为此,近代中国设立的佛教协会、佛教学院、佛教文化机构、佛教事业组织以及各类居士佛教组织等等,无不是太虚大师以佛教革命的手段、建立佛教社会形象的一种时代产物。而太虚大师提倡的佛教三大革命,也由此可被理解为以教理革命为基础、并致力于教制和教产革命的社会建构。
虽然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使命未能顺利完成,但是,太虚大师的三大革命的提出,却给中国佛教一个极大的历史启迪,那就是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必须具有一个社会基础,必须建有一个基于佛教信仰、佛教认同、佛教利益而自我组织起来的佛教社会。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教产需有社会制度做依托,教理必须进行社会实践,而教制合法性的取得和建构,则应当有一个良性的社会空间。由此观之,佛教形象的建立,其更深层的考虑,主要就是佛教社会及其社会形象的建构。所以,今日中国佛教的形象建设,在其使命承当上,同时也是对近代中国佛教传统的一个传承。
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佛教事业必须具有一个深厚的社会基础。缺乏了社会基础,佛教的公共形象就无法被真正地加以建构。单一的寺庙,并非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组织,简单的个人佛教信仰,特别是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曾经批评过的“寺院家族化”形象,[②] 实在是难以建构一个健全的佛教社会形象的。即使是佛教寺庙在其存在形态上,具有官寺、私寺、民寺和商寺的分别,不过是这些寺庙在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或文化资源的获得方式上的差异。至于寺院之修持型、经济型、文化型、园林型等发展模式的分别,则可以说是寺院功能的表达差异了。
由于中国人的佛教信仰模式,在相当程度上依旧是一种私人的、扩散式的信仰方式,他们对信仰的选择,不一定要皈依该信仰群体或寺院制度,所以他们的信仰表达,往往要依赖于固有的现实秩序或制度安排。[③] 所以,佛教寺院往往难以去强调一个信仰群体本身所具有的自我认同和自我组织能力。当佛教信仰在涉及、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时,其基本行动逻辑常常就是以个人的神圣崇信行为、精神个体的安身立命作为主要的考量原则,而非社会连带价值关联的社会行动,从而淡化了无数佛教信仰者的认同要求及其制度化运作形式,难以建构一种社会化、制度型的佛教认同模式。
为此,本文提出“佛教社会” 概念,并把它作为理解和讨论佛教公共形象的一个概念工具。首先是佛教的社会形象,其次才能谈及佛教的公共形象。这一概念,将表达出人们对佛教信仰结构、佛教组织的社会性、信徒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将把佛教寺院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一个类型,把认同佛教信仰的各种中国人组合为一个群体、构成为一种社会组织,使他们具有一种社会归属感,具有一种价值认同和彼此交往的价值关联,终而发挥出议一个社会系统应当具有的社会建设功能。
三.
按照社会学理论的定义,其所谓“社会”,作为人际关系的整合,是一切自我存续的人类群体,具有相对独立的行动领域,自身享有比较独特的文化和制度。就中国当代的社会建设而言,它应是国家与市场之外的一大领域,既与国家与市场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自成体系,独立而自在。
在经济力量极大地影响并改变了中国社会时,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同样也大大地改变了中国佛教的存在模式。于是,在国家权力与经济市场之间左右依傍的中国佛教,中国人基于佛教信仰而构成的“信仰共同体”或“功德共同体”的社会形象问题,自然而然,浮出了水面。倘若佛教信仰群体或者佛教寺院本身并非一个社会,无法建构一个“社会中的社会”,那么,佛教的社会形象就会落于虚空。只有寺庙,只有僧人,只有香客,只有功德。唯见香烟缭绕,不见真实存在。佛教之功德发挥,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就只能是国家组织的道德工程的参与者而已,佛教信仰及其群体组织也就始终成不了一个“社会建设的行动单位”。不是依附于国家权力,就是依附于经济市场,从而导致佛教本身的神圣性无所挂搭。
因为,这些佛教活动本身,并非一种社会组织的建设,仅仅是一种信仰功德的表现而已。其中的主要问题,绝非佛教公共形象的打造所能奏效的,而应当把佛教为社会所提供的信仰功德,视为一种以佛教信仰为基础的社会建设能力。
实际上,佛教作为制度宗教,其本身就是一种集中的、群体的、组织化资源,在其内涵丰富的“缘起” 观念之中,就包涵有共生和内在的社会依赖原则,社会成员和佛教信徒之间的“连带责任”。它们应能发展为一种复杂的、人际交往结构,进而建立一个对宇宙、社会的整体观见。
只是因为佛教的社会性表达和社会组织的建构,缺乏了现代社会组织应当具有的组织化、公开性、自立性三大特征时,它们就惟有左右依傍而无法自立了。它们无法构成“一个个人对另一个个人——直接地或者通过第三者的媒介——产生影响”[④]而变成的一个小社会。它涉及到佛教组织的建构模式、信仰表达模式、团契模式、身份及信仰群体的认同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佛教文化的信仰表达、人际互动、团体认同、人群信任……等层面的社会化建构路径。
对此现象,如以“佛教社会”的概念来加以检讨,那么,今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将有可能按现代社会需要的各种社会公义(justice)、权利(right)、非个人性(impersonal)与常规性(regular),建构一种“制度化行善”(institutionalized charity)的社会公共模式,把佛教对于行善布施和功德福报的强调,以建构社会价值整合的“连带关系”(social solidarity),即如何让寺庙、佛教信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社会活动的一个必要的构成部分。
因此,如何在社会建设的参与过程中致力于“佛教社会”的建构,把佛教信仰群体作为一个社会系统来加以打造,这等于给中国佛教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同时也为中国人反思中国佛教的信仰和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契理契机、自我建设的殊胜因缘。
--------------------------------------------------------------------------------
[①] 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刘威先生提出,寺院具有经济型、静修型、文化型、园林型,僧人具有社会活动型、文化学术型、宗教领袖型、闭关自修型等相关模式。本文参考了该说法,特此致谢。
[②] 太虚《建设中国现代佛教谈》,《太虚大师全书》,第9编,《制议》第33册,第277页。印顺《泛论中国佛教制度》,《教制教典与教学》,台北:正闻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③] 参李向平《信仰、革命与权力秩序-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相关论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④] G·西美尔(Georg Simmel)《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