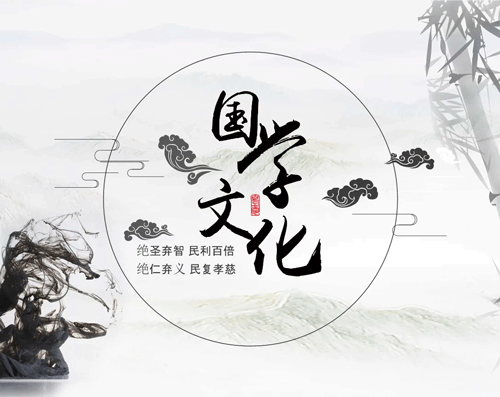佛陀的本怀与现实中的佛教
发布时间:2023-08-21 13:11:42作者:药师网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中国的高僧大德们,以及广大的佛教信徒在漫长的弘法、学法过程中,紧密依托于中华固有的文化背景,针对国人所特有的功利心态和宗教心理需要,在教义的研究弘传和修行的实践开展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佛陀的教诲和修学实践,作出了极富中华文化特色的诠释。但是,在这种理解的背后,也带来了令人遗憾的信仰错位——在部分信徒中,非佛法的思想及做法,在佛法的标签下畅行无阻。久而久之,佛法的精髓被抽空,佛陀的本怀被遮盖,成为部分佛教徒的信仰之痼。笔者从不认为当代佛教应该死守2500余年前的印度“根本佛教”(印顺导师语),即通常所说的奉行原教旨主义。佛教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日本、东南亚,甚至是在南传上座部佛教风行的南亚地区,都结合当地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仅是一种在坚持佛教的根本宗旨基础上的与当地、当时文化的适度趋同。本文就五个有关佛教信仰的基本问题,阐述笔者的观点。
一、佛陀的导引:
世尊他老人家的存在以及自身的觉行,非常具体地向每一个人和社团转告、展示并力图使众生做到:1.一种新的基本的定向和基本的态度,一种由佛陀带头并指出其结局的新的生活──人可以过一种更为真实、更为人性的生活,他们可将佛陀作为自身与人、社会、自然之联系、相处相融的具体的指导和生活的楷模。2.一种具有充分价值根据的行为动机成为可能,人能回答为什么自己恰好要这样而不是那样生活,为什么不应该贪嗔而应慈悲,即使在自己受到损害、迫害时,也应该诚实、仁慈、善良。3.使人能够把握并支持一种确定的一贯的价值意向:慈悲、正义、自由、慷慨、宽恕,即使在面临死亡,价值遭遇毁灭及自己受到威胁时也不放弃这种意向。4.使人能在孤立无助的状态之中,也能坚持自己的存在与创造,坚持更为人性的价值生活定向,人性的全面、完美、整体之实现,就是佛性完成的基础。5.使人能在佛国净土及人与人性的完成历程中,确定新的意义域和目的,使人不仅能够承受积极的人的生活,也能够承受生活的消极面,承受痛苦与死亡,并明确了知此消极面、痛苦死亡之源与实际内涵。
佛法的理论基础及修持之原动力均来自于“人生是苦”的价值判断。意识到苦,意识到人生的苦难、残忍、无道德性,是人性觉醒、回归之开始。怡尔的、平静的自然性生存,恰恰取消人的一切人性的东西,使之回归于植物性生存。审美式的生存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把一切虚无投入个体精神的怀抱──不管活人有什么样的痛苦,都要比充满宁静的、观念性“怡然自乐”要好得多。要将全部人生希望建立在实用基础上,甚至于以“钱”为生活的目标与奋斗动力,实在是人性自我湮灭的表现,是人类群体动物化的反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古训,已训示我们不要甘与动物为伍、保持相同的低层次的价值取向。佛陀的思想,就是要引导我们冲出动物性的桎梏,惊醒人们摆脱植物性的麻木。因此,佛陀将无明帷幕所遮的人类实际之境遇──“苦”之真象揭示出来,使人们能够得以脱离这种动物性或植物性的窘境。由此,我们在被佛陀敏锐、深邃思想所震憾的同时,不得不感怀佛陀的伟大、超凡:佛陀生于其母胁下,虽然奇特而却可信,由此显示其独特的清净;佛陀死于八十高龄,虽然平常但却伟岸,由此昭揭人生之真象。正因为其奇特而令我信,也正因为其平常而使人震颤。
二、做一个佛教徒:

做一个佛教徒,不仅没有降低做人的要求,也并不因此非使做人的要求变为虚无飘渺地不易把握,而是明确地提高了做人的要求:勿成为人,岂能成佛,连做人都处于迷茫之中,要想成为觉悟者,无疑是雾中看花、水中捞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做人难,做佛教徒更难。佛陀向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向仅仅是人类的自然性存在提出了挑战。一个人为什么要做佛教徒? 是因为要真正地成为人。这种观点,在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之人类主义的思想家中,也有类似的提法。但是,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西方的思想家要使人从教会的奴隶境遇中解救出来,可在同时却释放着人的作为动物的本能──无穷的情欲与贪婪性。这样的人能说是真正的人吗?如果是,那么人与野兽的本质区别又何在呢?连最低等的动物也具备情欲与贪婪的思维水平,尽管它们没人类的智商,无法最大限度地用技术来满足自己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欲望。现在的人被金钱、地位、名誉,甚至于住宅、学历、异性等等生存的因素所束缚,能说人是自由的吗?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人们一天也离不开电以及派生的各种电器设备,由于电脑的使用,再过一代人,可能连写字的工作均由电脑代劳,漂亮的、有生命力的书写文字将会成为稀世珍品。离开电器设备,人们将连生存能力都将丧失,只会如一只被人们宠爱饲养的狗丧失自我觅食能力一样。如此处境中的人,能说是自由的吗?与其说机器为人类服务, 到不如说人被自己创造的机器所束缚、所钳制。现在的人被各种欲望所趋赶,使自己的生存空间受到严峻的威胁───原因就在于无节制地消耗着各种不能再生的能源,将各种废料、污染物倾卸到地球的各个角落,这样的生存环境能说是给人带来自由? 与其说人类在破坏地球,勿宁说人在用自己欲望的力量为自身掘坟,在埋葬、消灭自身。进入十九世纪之后,各种政党、团体、政府、议员,都在不停地向人们灌输着不同的意识形态,用各种先验的预言、计划及成堆的文件,凭借着永不消逝的电波,向人们渲染各种感官的、理性的刺激,挑起了并且操作着千百万人去投身各种据说是能够带给人们美好未来的社会运动,愈益使人失去独立的、自由的分析问题、直面人生的能力与时间,无可奈何地随从左右着大众的生活模式,这能说是人的自由吗?无疑地,人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用自己创造的社会模式作为自身的枷锁,将自己锁上。面对着这样的时代,很清楚,我们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是无穷的难于填满的欲壑呢? 还是世尊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已发出的穿越时空,愈益证明其真理性的教诲呢? 答案应在不言之中。佛法不是悲观哲学,佛教徒也非虚无主义者,佛陀的教诲在于真正地提升人的人性,实现人性的完善化──佛性,以使觉悟之般若之慧能普种众生的心田,真正地使众生冷静、现实、清醒地面对我们的正报之地位与依报的时空状况。而作为佛教徒,其首要的是什么呢?而所需做的又是什么?
关于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佛教徒,众说纷云,莫衷一是。笔者认为,所谓皈依某个法师,发一个皈依证,这仅仅是佛教徒的世俗手续和方法,这在现代社会流行,作为方便法门未尝不可。但是三皈依的内涵决非此方便法门所能包括。现代佛学中有一种观点,很值得受过三皈依的众生再三寻味:佛、法、僧三宝并非偶像,这三者作为一个统一体,也不需你顶礼膜拜;这三者作为象征,要你在顶礼时认识其真正的内涵,即皈依自性的觉、正、净,使每个众生内在的、本具的佛性──觉、正、净显发出来。由此,作为佛教徒,首要的就是要认识佛陀,佛陀是觉、正、净的典范;研读经论、聆听讲经说法,就其根本目的,也在于认识佛陀之觉、正、净的具体内容。但是,光有一般的认识是不够的,如果不把自身的觉、正、净诱发出来,那么,你仍然是一个凡夫,迷、邪、染仍然如影子般随着你,如寄生虫般依俯于你。由此,作为佛教徒,都有一个“我应该作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佛教的三藏中都有说明,而对于当前的婆娑世界众生,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用你对于佛陀的认识,尽量地依教奉行──依照佛法的教理去返观世俗世界,重新认识你天天生活其间的世界,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我们之所以对世俗的世界不能清醒地认识,是因为我们是用世俗的观点思索世俗世界;如从出世的角度,借助于佛陀超凡的认识力量与方法重新观察世俗世界,相信你会视世俗世界忙忙碌碌、盲目奔波追求的众生犹如一群蚂蚁在社会中无意义地、渺小地生存、喘息。这时,你即会对世俗世界人欲横流、舍本求末的现实深感可笑、可恨且又乏味,又能够自然地对芸芸众生产生最为深沉的、真切的、决非是廉价的悲慈体恤之心;而且由此也能真正地体会到佛陀觉世工程的宏伟与悲壮,体会到你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价值与作用。有了这现实而正确的第一步,作为一个佛教徒,就能够摆脱一切世俗的桎梏,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在这样的先决条件下,戒定慧三学、六度四摄、三十七道品、止观等等修行法门,才会化为自身的自觉行动。佛教徒,担当的是续佛慧命的重任,具有使法轮常转的义务,任何一个佛教徒均不能仅仅将此视作为口号或旗帜,而应化为自己在娑婆世界中的行为,并以集体的力量,共业所成,使芸芸众生一起趋除黑暗,挣脱生死物欲的黑洞,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三、对佛陀的信仰:
谈到信仰,似乎这个问题只能够与那些准备信仰某种宗教或已经信仰某种宗教的人来讨论。此问题其实应是社会任何一个成员所实际面临的事实。一个人可以终身不信宗教,但它却不可无信仰;为人可以一辈子不走进寺院教堂,但他却必须面对自身。信仰是人的精神之直面自身后所寻求的目标归宿,它是抉择的结果,也是人生意义的开端、基础;是人生旅途中的导航仪,也是个体生存的动力;缺乏任何信仰的人是行尸走肉。但是就如我们前述的,人是有信仰的,但不等于他信仰宗教,更不等于非要信仰佛教。既然信仰是个体自下而上的抉择,那么,信仰就不应该是盲目的,而应该是负责的。人不应该受到精神上的强制,而应该在理性上深信不疑,或者在感性上达到某种自明,不带任何功利的急切的渴望。由此他才能够作出可以辨解的、自我能够感到踏实安稳的信仰抉择。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信仰不应该脱离实际,而应该联系现实,人不应该不加检验地获得信仰,人的陈述应该通过与现实的接触,在人和社会现今经验范围内加以证实和检验,因而得到现实具体经验的容纳;其次,同时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理性和理论性思维是有局限的,这种理论的理性的局限性,也揭示了我们局限于人类现有的经验范围,超越于我们经验范围的事实,我们的理性是无权判别的,正如未被实验观测所验证的理论,无论如何完美和精致,都仅是一种假设。我们知道,科学中有很多种理论(如物理等),在外行人看来每一个公式, 每一个定律都是那样的准确无误;但科学家们知道,这些理论的生命力只在于其近似地解释了我们所知道的经验,而事实到底是怎么会事,也许永远是个谜;就连我们是否该解开这个谜,如果解开这个谜,对于人类意味着怎样的后果,也不得而知。其实,在很多时候,理性告诉我们的和经验展示给我们的,并不一定是正确的、准确的,而是不真实的、或者不完全真实的,对于此点,佛学与科学从不同的方面给予了回答。以佛学之见,任何客观的事物,都需由人的主观去认识,去辨别分析,然后才具其意义;即色与识的关系,色与识──主客观是相对应的,但并非平等。在此,主观(识)是起主导、支配作用的。由于主观的支配作用,我们所认识的客观,永远是被主观所加工过的。因此,绝对客观的东西,只能存在于人类一厢情愿的想象之中,而在身外无处可寻;这也就是“万法唯心”、“识有境无”之教义所要昭示给人们的。相比之下,科学家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还是本世纪由于微观世界那样超乎寻常的难以把握,由泡利等人被实验弄得束手无措之后,才恍然大悟。总之,我们所感受到的世界,永远是被我们主观所笼罩。由于每个人的主观都是有差异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并非一个。而是有千百万个:“每天清晨有多少双眼睁开,有多少人的意识苏醒过来”,便有多少个世界。
上面既强调了信仰离不开现实,又强调了现实的理性与经验的不可靠。貌似矛盾,但是,这就是信仰者的真实心境,信仰的力量来自于现实,但是信仰又恰恰是对现实有所批判与扬弃的。同时,信仰作为宗教术语,又绝非它在西方日常用语所指的意义:对某种人既不能精确认识,也不能加以证明的东西,给予理智的和情感的承认。因为,这个定义的重点是落在逻辑规划与经验证明的方法上,使信仰变成盲目地认同不确定的、扑溯迷离的事物的代名词。其实,信仰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也不仅是一种认识论类型,而且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把日常生活置于永恒的、终极的真理或实体之笼罩中。这种信仰的行为不仅使人精力充沛,而且使人获得一种信念,即人们可以从至善的无限力量中获得最深厚的充实感。由此人们把自己的生活转向最高的精神目标。无论生活风行什么,他们都会充满力量、觉悟与安宁,并且高高兴兴地为他人服务。所以,宗教的信仰与世俗的信仰不同,其要点在于两方面:宗教的信仰主要是情感的,但并不排斥理性,而世俗的信仰则主要是观念上的;宗教的信仰将融化于个体生存的生命体中,而世俗的信仰则主要是认识上的、方法论的。就其实质而言,信仰宗教的个体之主要表现形式,是宗教徒体验到只有依赖于彼岸的或超然的力量才能够获得拯救或依托的力量;信仰实质上是确信这种力量能够更新自己的生活。佛教徒同样如此。这里,“彼岸的力量”或“超然的力量”可以表达为出世间法。问题在于,不少人喜欢钻牛角尖,如你不向他们说明西方净土到底在何处,是否如我们生活的世界一样是个实体,他们就不会去相信,不会投身于此。于是类似《阿弥陀经》之类的经典就适应此类根机众生而产生了。实际上“彼岸的力量”自身是模楼两可的──由于“彼岸力量”的疏远性,既产生了确定性,也滋生了不确定性。应该说,有信仰的人总是处于了解与学习的开放状态,而不是处于偏激状态。如果处于偏激、偏执的状态之中,其信仰的对象由“彼岸力量”异化为自身的执见。所以,一方面,信仰包含着对于“彼岸力量”──佛陀的先知先觉所指引的解脱之道的直接的和及时的认识;另一方面,这种认识的对象(佛性)又完全不同于人类知识中的常见现象,而是一种令人扩展并且支配人的力量,它打破了那些旧有的、便利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其确定性在于佛陀的觉悟与昭示的解脱之道之真实确然不谬;其不确定性,在于我们凡夫的认识能力千差万别,无法用统一的、一以贯之的方法理解,因此相应的随机说法,就很不确定。从另一方面观之,确定性是彼岸力量真理性的体现,而不确定性则是其丰富性的体现。
我们也不能将信仰归结为对于事物的根本性质的一无所知,那种偏执于不需搞懂教理就可以修持佛法的观点,在佛教徒中颇为流行,甚而将教理研究者一律视之为执著于文字,无法了生脱死,这不但是一种有害的观点,也是对佛法的歪曲,根本上降低了佛教徒的宗教修养,失去了抵制外道邪教的能力。佛陀的信仰者,是解行并重的,这种信仰是在“戒定慧”三学中,对佛陀作出的自觉而肯定的反应;在“解行”中增强信仰,并融化于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结出圆满的果。不能将对佛陀的信仰高悬在理性上,也不要堕于俗务中。而是须将佛陀的教化晓之于理念而又行之于实际。
四、对佛陀的崇拜:
对教主佛陀的崇拜,是每个佛教徒必有的心态。崇拜意味着内心的感受,这是对于佛陀的赞美、信赖与深深的敬仰。对于佛教徒而言,向往进入佛陀的觉悟之道,祈盼将解脱之道化作个体的存在,这种崇拜就成为一种独特的必不可少的活动。有弘法大师曾将我们拜佛的举动用中国古时学堂拜孔子、拜先生的礼仪予以诠释,这对于打消人们蒙在拜佛仪式上的种种迷信心态,不愧是通俗而又有效的诠释。但如深究,拜佛仪式与拜师礼仪曾有相通之处,而其不同点又是主要的、显明的。拜师是国人尊师重教、敬仰文化人的传统之体现;而拜佛则是对于佛陀的神奇的觉悟之性、伟大的智慧之光、不可思议神通力量、广大的慈悲心及其震憾人心的解脱之道的崇拜。因此,这种崇拜是一种向上的行为。它使个人经验地意识到佛陀的现前存在,崇拜不仅使灵魂充满了欢乐,而且用令人获得新生的生命之泉沐浴了整个内心世界。没有获得这种个人追随佛陀的欢乐体验的人,肯定没有获得最丰厚的恩惠,也肯定不能获得宗教的最高法乐。在佛教中,崇拜的外在表现是拜佛、诵经、持名念佛等等,这些外在表现只有同众生的内在崇拜心态相一致时,才是最主要的,才是有效的。而这种内在的心态,即是祈祷与感恩。我们教内的信徒们往往不习惯这二个被基督教所常用的概念,其实,我们在与佛陀的交往中,所缺少的正是这种祈祷与感恩的心态,致使教徒们太多地带上功利性色彩。
祈祷,在佛教中本来早已有之,有仰求佛菩萨之冥助,祈得除灾增福之义。但是这一词在古代印度的佛教文献中就很少出现,其原因主要有二个:第一是,因为佛教从究竟的意义上而言,是自力的宗教,而祈祷的崇拜形式,则明显地带有外力的性质;第二是,在婆罗门教中,有祈祷主(Brhaspati Brahmanaspati) 的抽象神存在,而这一神在印度教中,又演变而为木星之神。佛教在历史上以无神论及反婆罗门而著称,故很少使用祈祷一词。到了近代,随着基督教传入佛教流行地区,汉语中将基督教信徒与上帝和基督心灵直接相通的方式──Prayer译为祈祷之后,佛教使用这个词的频率就更少了。其实,佛教在近代的发展,祈祷的仪式还是被逐步重视的,只不过佛教界内部至少存在着如吕澂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三种弊端,改变了这种祈祷仪式的神圣性:第一为呆板泥迹,专讲婆诃苦恼、生死可畏的一套话头,引人厌世躲闪,这种思想是由声闻佛教引申而来,但是却全没有小乘佛教的严肃深刻精神,只剩有浑身的自私自利的解数。只要到香客中去听一听他们对于佛法的议论,就可见其一斑;第二呼禅蹈空,专唱高调,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说得一片响,完全不着边际,这必将引向浮泛空虚,于佛法却一无所得。这一点,在现在不少出家人中有成风之势;第三为纯玩概念,专究学理,无论是说生道死,谈空说有,一律从知识论的角度予以理会,只图说得顺口动听,不管与自身的切身之关系如何,更不理会与此人世如何衔接。结果是一场空话,与现实的人生漠不关心,毫无作用;这以搞佛学研究的人为主,他们逐步地将佛法引向一门纯粹的过去时代的学问,将佛学请入了人类思想博物馆供人瞻仰。这三种弊端使佛教中对于佛陀的崇拜祈祷仪式成了不伦不类的东西。第一种弊端使祈祷成了功利性的、利已的手段;第二种弊端使祈祷形式成了一出常演常做的滑稽戏、毫无真诚感人之处;第三种弊端则对祈祷予以排斥,将其视作为村民野夫的蠢念愚举。在这样的氛围下,佛教中对于佛陀与菩萨的崇拜、祈祷仪式,不能不时常处于如下的尴尬境地:或被皇帝、政府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或被僧众作为装门面、谋生的一种方法;或被信徒们作为谋取私利的表达形式。这实实在在是一种误区,是一个陷阱。
其实,尽管佛法是自力的宗教,可我们凡夫毕竟是依仗佛的启导、开示才认识到人们的实际境遇与应该走的出路的,我们也毕竟要真心诚意地皈依佛法僧的。只有在上述的基础之上,才可谈及自身的努力。所以成就佛性,是佛力与自身努力的结合之结果,不能撇开佛力谈自力。正因为如此,对于一般凡夫而言,祈祷是使自己的生活佛化,使自己的身心与佛陀之觉性交流的重要途径。除了用有限的智力去认识、理解佛法之外,祈祷是我们与已辞世的佛陀交流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是个体的,每一个个体的体验是各不相同的。因为佛力用我们的肉眼凡胎所无法感知,所以我们只能祈求佛力的“冥助”,这种冥助又决定其是个体化的,是秘密不定之法。冥助我们什么?这是每个个体的事, 但又具有一定的共性,并非我祈求什么、观想什么,佛陀全会满足我们凡夫的奢欲俗望。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祈祷是很重要的。我们祈求的只能是佛力加持我们孽障深重的人生,使我们少一点业障,多明佛理,接近佛陀;一句话,我们只能祈祷佛力加持我们,让我们接近佛陀,在佛陀的智慧照耀下完成升华,实现佛性。除此之外,一切祈祷都是世俗的,是为佛的究竟法所不容。
在佛教中,有回向的仪式,所谓回向(parinamq),在一般的意义上是指以自己所修之善根功德,转给众生,益使自己超入于菩提涅磐;或者以自己所修之善根,为亡者追悼,以期亡者超脱三恶道。这固然是慈悲心之体现,可在佛教中是否有回向于佛呢?乍听似乎佛并不需要我们的回向,可是我们众生从佛处祈求得到了无上道,也应该有所回向,这种回向就是报佛恩,而要报佛恩,就必须有对于佛由慈悲心出发对我们众生的无尽的恩赐的内在的、由身心而发的感激之情──感恩。感恩的心理,是对佛陀崇拜的另一面,是个人对佛陀之觉性解脱境界之体验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培养这种感恩心理是走菩提道的基础,也是报佛恩不停留于口头上的保证。
有人可能要问,我们说对佛陀要崇拜,并要有发自内心的祈祷与感恩,这是否有将佛陀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God)?要知道,佛陀本身是一个人,而且佛教是无神论,又是竭力反对一切对于神的祭祀的。但是,笔者认为:现在佛教界高唱“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强调自性即佛,拜佛即拜自己。这固然动人悦耳,似乎也与究竟法门相契合。问题在于,任何事物、理论,如没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推向绝对,就会走向其反面。在这些高调的深层,我们既失去了自性,也寻找不到佛陀;在动人的口号中,我们的凡夫我慢之心得到了高扬,一切世俗的东西以合法如理的面目出现,成魔之人与成佛之人难以分清;缺乏了佛的神圣,冒充神圣者却充斥于世,这样的情况我们见的还少吗? 某地一个黄毛小孩竟敢自称“无上师”,而多少人却趋之如鹜地拜倒于这个一会儿在家、一会儿出家的“无上师”脚下。由此我们对于佛陀应该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佛陀虽然是一个人,但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圣人或伟人,而是觉悟的佛,与我们凡夫相比,他是创觉者。他的觉悟并非仅停留于书斋与笔端,而是由自身的身体力行证实般若智的佛陀──大雄。我们不能忘记佛陀与我们,即凡夫( 一般的圣人、伟人只不过是凡夫中之优秀者)之间有着无限的距离, 这个距离只是依仗佛陀的无限慈悲、方便善巧、无尽愿力,才使之消除,难道我们不应向佛祈祷、对佛感恩吗?同时, 这种由佛出于愿力的不可思议而衷心所希望成就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并不能消除我们与佛陀之间的实际距离。其原因在于,佛陀早已给我们点明:凡夫在苦、惑、业中翻滚,世俗的各种束缚,使我们难于接近他。佛法强调修证,就在于强调我们要去打破难以打破的束缚,去接近佛陀,而这是要靠我们脚踏实地、循序渐近地进行的。可我们更多的信众,只是在理性上同意他老人家的观点,在学术上阐述他的教义,而在具体个体生存中,则与之不相协调,甚至南辕北辙。
五、关于信与解的问题:
人类的理性可以达到与佛典及其佛陀、佛弟子的开示相符合的结论,因此,我们在学习佛法运用辨证法的推理,可以将教义当作是有待证明的结论,而不是证明的前提。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思考中不能够仅仅靠经典的权威来论辨,而要简炼地证明理性必然性,不管宣称什么样的研究结论,都要公开地显示出真理的明晰性。旁征博引固然能够证明真理的权威性与共识性,但是,以逻辑所要求的简明性与必然性论证信仰的真理性,则对于真理的认识与把握,显得更可靠。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信仰所坚持的,与被必然性所证明的是同等的。因为理性有其力量逼近真理。
但是,我们也不否认,逻辑推提可以达到与信仰不相符合的结论。在此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理性的结论与信仰不相符合时,如何来判断是非?第二个问题是, 如何能够防止理性与信仰发生矛盾? 第二个问题要由佛法对于我们人类思想方法的总体检讨与细节辨析去把握。在此我们不论。关于第一个问题,则笔者之见是,以佛陀的圣言量为标准判断是非(当然,由此给研究者提供了又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即如何去判断汗牛充栋的佛典中,哪些可谓圣言量?而哪些是方便施机、对机权教?) 如果我们在理性研究中,说了一些圣言量所未提及的话,即使我的述说对我而言是理性的必然之结论,我们还应以如此的方式接受这一述说,即它不被说成是绝对必然的,只是被说成是现在看来似乎是必然的。在原则上而言,必然理性不可能与信仰发生矛盾。如果发生矛盾,则说明理性并不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以佛陀的圣言量为准,因为佛陀的圣言量反映的是对诸法的真理性认识,我们的凡夫理性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怀疑的。有见于此,笔者认为,个人的理性不具有必然性。对此,我们只能在佛前作如此的表露之愿:佛陀世尊,我渴求达到你所证悟的究竟之境界,但是,作为凡夫的我,其理解能力根本不能够与佛的崇高之境界相比拟,我们单凭理性完全无能力这样做( 所以佛要求我们不仅有信与解,而且要有行与证,不过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在此不讨论)。但是我渴望能够理解你的那个为我信且爱的真理, 因为我决非理解了才信仰,而是信仰了才理解。
在第一点中我们强调了理解信仰,第二点中又强调了信仰才能理解,二种说法都是我们的立论,但其中似乎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与佛经中常出现之矛盾类似,属于徉悖论;根本上而言,二者并非矛盾。因为,由信仰然后理解,其说明的是思想认识的顺序;而由理解来确认信仰的真理性,则是语言论辨的顺序。我们对于外部对象的辨认,一般有三种方式,第一是通过语言符号,第二是通过思想观念,第三是直接辨论。如果被辨论的对象是佛陀,那么,第一种方式便是信仰,第二种方式便是理解,第三种方式便是论辨。只有已经信仰佛陀的人,才能在思想中形成关于佛陀的观念,通过这些观念理解佛之法身;语言表达观念,论辨是运用语言表达被理解的观念,终归要以信仰为理解的条件,然而在论理中,我们以被理解的命题为前提,证明信仰的真实性。论辩不过是人的实际认识过程的逆向运动,它不以信仰为前提,但并不等于说在进行论辨之前,人们对论辩的对象没有信仰和理解;相反,论辩按照语言的逻辑顺序,把理解和信仰的内容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人类的语言以抽象和概括为基础,不能完全表现在信仰中以直觉而认识的佛陀及其博大玄妙的觉境,这也是为什么论辩常常会出差错,推导出与信仰不相符合的结论的原因。但是,语言在佛法中被一针见血地定义为“假名”,在某些宗派中(如禅宗)甚至提出“不立文字”,而佛法之精髓又是表现为彻底的“ 亡言绝虑”;尽管如此,佛法还是用语言表达, 禅宗仍然靠文字在流传。这是因为,语言的中介犹如是一面镜子,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信仰的真实性,以及对于信仰的理解。
既然对于佛陀的信仰在佛陀在世及其圆寂后不久,既由其本人的伟大先觉以及弟子的闻声得悟所确立,这种信仰,是否还迫切地需要用逻辑的方式重新理解与表达?笔者认为, 佛陀的真理是无比崇高的、无比博大精深的,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没有人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穷尽佛陀的真理,即便是他的及门弟子也不能够例外。实际上,不将信仰放在第一位是傲慢,而有了信仰之后不再诉诸于理性是疏忽,这两种错误是都要加以避免的,在佛学的发展道路上,这两种错误都是同样的存在,而且推向极端,都是危害正法长驻于世的。其实、信仰与理解无法分开,每一个个体都必须自己信仰,又要自我去理解。
信仰是理解的出发点,没有信仰,就谈不上理解,我们要在对佛法的信仰上去寻求佛法的理解;而有信仰,并不必然地总会伴之于理解,理解不会因为信仰而自发产生,理解是理性积极寻求的产物。信仰之所以要求找到理解,并不是出于某种逻辑的必然性,而是出自于对佛陀的皈依,出自于对于佛法之真义、要义的发掘之渴望;由此,理解并非是冷静而枯燥的逻辑思维,它伴随信仰的情感因素,不然,这种理解就仅是一种学术活动了。理解信仰,在佛法中占据着由信仰上的情感活动过渡到身心的实践佛法、彻悟与证知佛法的中间位置,究其本质,理解的起点与终点都是信仰,是一个不断深化信仰、把信仰由盲目推进到正知正见以至于实证的过程。所以,理解也必须接受信仰的不断检验与督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