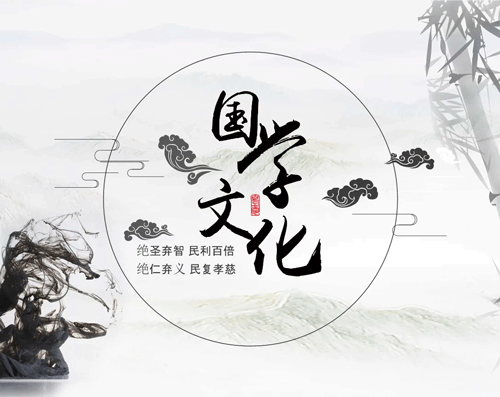苦待
发布时间:2024-02-01 11:34:26作者:药师网苦待 天还没亮她就醒了,一醒了就没法子再睡。她心裹有事,丈夫又在身边大声地打鼾。她一按床头开关,小灯泡亮了。在那五支烛光的光线下,她看见丈夫的头已经越了界,侵占了她的枕头,他张着嘴,口涎从嘴角流了下来,喷出一口一口的浊臭,使她闻了恶心。她嫌恶地翻了个身,背着他,可是熟呼呼的口氧又吹在她背上,使她觉得非常不舒服,一翻身坐起来,两手支着床,侧着头,瞪眼看他。丈夫的秃亮大脑袋占她半个枕头,狮子鼻张得很大,一鼻孔的脏污,一脸花白的短短络腮胡渣,两道倒垂的疏眉; 一只痴肥的臂膀露在被子外面,上半截是光滑的肥肉,到了靠近手腕的地方却不伦不类的长了些疏落的毛,又粗又黑,那肥拙的手指的背上也像刷子般地长了汗毛,中指上戴了一只汗积斑斑的墨绿戒指。她看了他几眼,心中有说不出的嫌恶感觉。她有些不懂,何以自己竟能和这样的一个人同床共枕了快二十年。是的,二十年了,为什麼直到今天才发现自己对他嫌恶。她忿忿然地推了他一下,他的胖肉颤动了一下,身体却没动。她气得很,捏起拳头,恨不得槌他一顿,可是立刻又将气嚥下去了。她觉得他可恶,但是立刻想起: 二十年前的他,原来并不是这样子的。那时候他虽不漂亮,但的确没有这样痴肥。那特候他有一身结实的肌肉,和一张拙朴而诚恳的脸,一双三角形但是充满熟情的眼睛,还有一颗不坏的心,这颗心和她结合了二十年,经过多少患难,从贫穷到现在小康,他对她的爱意没有半点松懈,她也从来没有感觉他可恶。然而今天,她却厌倦他了。就是为了他的睡相麼?那麼简单?她早已看习惯了。她自己知道是为了什麼。只是为了好友梁太太的一句话:『 祖义回国了!你知道不?』祖义?啊!祖义!听见这个名字她就心慌了,像给雷击一般,好半天都不能动弹。『 人家说明天要来看看你呢!你得好好准备一下!』梁太太说:『 他一回来就到处打听你,不知道什麼人告诉他你们来了台湾。昨天在校友欢迎会上,我们老头子把你的情形告诉了他,还写下地址给他,他说一定来看看你,明天一早就来!』梁太太是她的老同学,昔年一同在校园裹荡秋千,也一同逃学去看嘉宾的电影,彼此交换过少女心中的秘密。昔年她们是留着留海的白衣黑裙小姑娘,如今却都已进入中年,儿女成群了。隔别多年,她们在此意外相逢,感情更加浓厚,两人的家境都不错,丈夫又都是商界的成功人物,住得又近,所以来往就很密切。这天晚上,梁太太特地乘着她的先生不在家,跑来告前她是个消息。『 他回来了?』她有些神志不清地说这句话,似是问话又不像是问话。她本来想要矜持一点,不露出心中的激动。但是在适个交换过秘密的好发面前是无法成功地掩饰的。『 是的!难道你真的不知道?』 梁太太说:『 他是回来参加一个什麼会议和庆祝国庆的,昨天新生报上把他的名字登了那麼大的一个,你都没看见?』 她摇摇头。她看报是向来不看大事的,只看武侠小义和社会新闻妇女家庭之泪而已。她的时间都消磨在牌桌上和串门子上。她也念过大学,可是由於生活优裕,不需要做事,她也就不理会书本报章了。梁太太拿起报给她看,黑色的铅字跳进她的眼帘:『 我国旅美名科学家祖义博士,今日返过国参加我国首次原子能科学发展会议。祖博士为我国驰誉国际之物理学家之一,原籍河南,今年四十三岁,XX大学毕业。旅美研究原子能二十年,此次为首次返国。祖博士今日乘民航公司超极翠华号自东京飞抵台北,到机场欢迎者xx 大学校友多人。他在机场接受记者访问时称:此次返国,除参加原子能科学发展会议外,将在各大学讲学数日。』後面有一篇简访记,介绍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记者问他此行何以不舆夫人同行,他苦笑着说还没有结婚。记者问他为什麼事业已有成就了还不结婚,他说结婚的契机已过去了。记者描述他言下似有无限心事,不便多问,就打趣地问他是否有意在国内物色佳人,他微笑着说:『也许吧!』 那篇访问记上还有他的一帧照片,可惜是和欢迎者合照的,人太小,看不清楚。她捧着报,报在她手中颤动不已。『他终於成名了!』梁太太说:『 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可是,他还没结婚!你想是什麼缘故?』 『 是的!』她答非所问地说。她的心慌得属害。刹那间,往事的片段,千头万绪,一齐涌上心头,每一件事都那麼清晰,又那座模糊,记不清那一件在前,那一件在後,可是都沥沥如在目前。『 祖义!』她记得很清楚,自己曾经无限诚恳地向他说:『 我等你,等到你学成归国!无论多久我都会等!』 她记得他说过:『 除了你,我是不会和别的女子结婚的!离一你等不了,嫁了别人,我也就只好献身科学工作了!』她记得他的低沉的、富有男性魅力的声音,他的灼熟逼人的眼睛,两道浓眉,瘦削内陷的双颊和挺值的鼻子,还有他的经常都像是在咬着牙的神情。他盆并不算是很漂亮,可是有一种逼人的力量,有可以熔化铁人的熟情,和一种丈夫气概,还有崇高的理想。他的温存的、但是充满着保证力量的笑容仍然清楚地留在她心上。二十年了,这个可爱的笑容不时从记忆的暗室中逸出,但是没有一次像现在那麼清晰新鲜。
那真是魔鬼的安排,如果不是遇到是个个在是她丈夫的男人,她是断然地遵守自己的诺言的。起先,她根本不理会这个男人,因为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他都不如祖义远甚,尤其是当她现在看他躺在身边的那副睡相,更觉得他令人恶心。当然,他常年也曾经是个好青年,有熟情,不算丑,可是此祖义就差得远。不过他的追求是此祖义更进一步的,他的外表纯朴忠厚,却懂得尽力讨好,逼得她穷於应付。他的忠厚相貌帮助他成功地做了一件最不忠厚的事。她接受了他的一个普通的邀请,在他家中和一些同学聚餐,结果,他在她的饭後咖啡裹放了些束西,使她酡然不能自持,任由他摆布。终於,在哭了一大场之後,因为生米已成熟饭,只好做了他的太太。起先,她是恨他的,渐渐地,她发觉他毕竟是个忠厚的人,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爱她,求她的原谅。他服从,像奴才般地服从。他将所有的收入交给她支配,多年来,他在外面的私生活也很严谨,偶而逢场作戏,却绝对不敢迷恋下去。由於他的稳实作风,使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中等商人了。最难得的就是,他顺从如旧,忠心不二,她有了经济实权,又有了四个儿女,她已经满足了。她的心境就像是一泓清水,现在,祖义的名字却像一颗石子般地,投入了这泓清水之中。祖义的音容笑貌,涌上了她的心头,使她一夜无寐,刚睡了一下,就惊醒了。醒来,看看丈夫,越看越厌,抓着床头开关,索性把这五支烛光的灯关了。在黑暗中觉得好过一些,可是不到一会儿,窗子外面的天空已经现出了鱼肚白。街上有了汽车飞驰和行人的声音。她索性不睡了。睁眼看那天空的微曦,心中在想,他为什麼还不结婚呢?难道真的是为了他说过的那句话?那麼认真?想到这一点,她的心就狂跳。那已经失去的、青春初恋时的那种慌乱感觉重新涌上了心头。她这些年来都没有太多的後悔,现在却後悔了。她以前虽然也有对不起他的感觉,却总认为自己没有什麼责任。现在,她不由地後悔自己当时心肠太软,竟不能拒绝一个自己不喜戳的男人的邀请,而且,太相信『 皮相』 。固然,丈夫并不是壤人,可以说是个无可非议的丈夫。他的体贴和服从,以及宽裕的物质生活,原都无可指摘,现在,却忽然都燮成可恶的束西了,好像一切都无以补偿她的损失。祖义!啊!他是不是真的会来呢?他真的还记得我?他明知我结了婚,有了儿女,还会来看我?她觉得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像是肯定的,又像都是否定的。她听见大女完在催弟弟妹妹起床上学。她每天早上,一听见女儿的声音,就披衣起床看看他们,她总是不放心,怕下女给他们准备的便当菜不够营养,又怕菜馊掉了。她会叫儿子女儿添件衣服,给他们一点零钱,然後再回去睡。她好费劲起来,披着睡衣,睡眼惺忪地拉开纸门,越过客厅,走到孩子们的房间,看看没有什事,说声再见,又回到卧室来。她坐在梳妆台前,朝镜子看看。这时候光线还暗得很,她拧开台灯,镜中显出了一个满头发夹的憔悴人影,两道眉已经不见了,眼尾有些向下斜,而且起了一大把鱼尾纹。眼[+(-月)] 是浮肿的,带着紫黑的颜色。两颊韵肌肉松弛了,毫熟血色,垂了下来。虽然仍有美丽的痕迹,但是真正的艳丽和青春,已经移交给十九岁的女儿了。她轻轻的叹了一口气,拿起一把发刷,看一看,放下来,又拿起眉笔,刚要画,发觉还没洗脸,就放下它,向浴室走去。她自觉步伐已无复昔年的矫捷了,然而,不知怎的,心中就不相信自己就是镜中那种憔悴的样子。她的心中似乎不断地在呼唤:『 祖义!』一种青春的感觉充满了她的心房,只要想到这个名字,人就年轻起来了。她再回到卧室,就坐在梳妆台前刻意地打扮起来。她带发夹取下,用心地将每一根头发都刷得伏伏贴贴的。她才做了头发两天,否则她就打算上美容院了。她很知道,刚刚做的头发是不会太美的,做了一两天,才显得得自然,所以她很庆幸前天才做了头发。她很仔细地在脸上薄薄地匀一层粉底,然後轻轻拭掉,才加上一屠『庞斯』 ,抹一点胭脂,使自己看来有些血色。找出一支半液质的浅朱色口红,用小刷子沾了,细心地描出美丽的唇形。装上一付颜色不太黑的假睫毛,可是立刻又把它扯下来,她想起祖义是不喜欢浓妆艳抹。不过,她还是用眼睫毛夹子夹了一下。之後,她画了两道并不合适宜的淡谈蛾眉,因为,当年是时行这样的,她足足弄了一个多小时,才算勉强满意。
丈夫起来了,只看见她坐在镜前刻意打扮成这样淡雅的样子,觉得很奇怪。『怎麼啦?太太!』他走到她身後,痴笑地问:『 今夭变了样子啦?』 她从镜中看见他的痴肥和凸起的大肚子,觉得恶心,於是紧闭着嘴,不理会他。『 嘻嘻!淡扫蛾眉朝至尊!』 丈夫虽是商人,却懂得风趣:『 我变成唐明皇啦!』对於他的阿谀,在平常,她是会高兴的,可是今天,她就是不高兴。她也不发作,也不讲话,只是揽镜自照。『 怎麼不理我呢?』 丈夫明知碰了钉子,还是说下去:『 你今天好像很有心事嘛!』 她猛然地回或瞪他一眼,说道:『 什麼心事不心事,你管我的!』 『噢!噢:…』山丈夫一急了就录说不出话来,只好堆起一脸[言+焰-火] 笑。看见他著这样子,她霓觉得越发可恶了,仿佛从他的身体上就可以嗅着铜臭,她向来不觉得他俗气,今天却不然。『 你不是说今天有事要亲自到基隆去一趟吗?』她说:『要去还不早点儿去?』『 才七默点多呢!用不着这麼早。』 『 早点儿去!』她命令地说:『 早去早回!』『 好吧!』丈夫拍拍大肚子,(口+奴) 高了嘴:『太太不高兴,太太有命令!我只好早点儿走了,早餐也只好外面吃啦!』她并不讲话,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兀自照镜,吹毛求疵地弄头发,连一根短发都不放过。表面上,她是矜持的,其实心裹乱糟糟。过了好半天,没听见丈夫的声音,门外却声起自备三轮车的铃和大门开关的声音,她知道丈夫走了。忽然她又後悔起来,不知那儿来的一阵冲动,竟使她伏在梳妆台上哭了,这是很奇怪的,像她这种已经四十岁的女人,感情应该是很能控制的,而她这时候竟然会失去常态,像孩子般哭。幸而她也只是滴了不多的几滴眼泪,那种苦楚就飘然而去了。她给起头,觉得心中空空的,有一种强烈的怅惘感觉。祖义是不是真的要来呢?他来了,又怎样应付他呢?他现在是什麼样子?他的惑人的笑容是否仍然和当年一样?他来了,应该如付何接待?说些什麼话?尤其是第一句话该怎样开口?『祖义!』她将要低声呼唤他,努力保持声调的平静。可是,这一个低声的演习,却是失败的,她的声音颤抖了。『……』祖义一定是沉默的,就像当年一样,默默地站在她面前。她必须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她怕会再投到他怀中,虽然她知道,今生今世,永远不可能再投到他怀中了。是的,她只能远远地望着他,『请坐!』 她第二句话要这样说。可是,他是不会坐下来的。他只是呆呆地站著,向她凝视,他的眼睛没有变,一样闪烁著(火+勺) 人大光芒,但也两鬓有了星点了。那样却反而使他更显得有风度。第三句,她将要说什麼呢?难道两人就这样相对,默默无言下去?『 太太!』下女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吓了她一跳:『今天买什麼菜?』『照前天买吧!』她不耐烦的将钱交给下女。下女走了几步,忽然又给她喊住了。『 来!阿英!』 她另外拿出一点钱:『 另外买些鸭[月+屯]肝,五香豆腐乾,再胃一只鸭子清炖。』她把祖义爱吃的束西都报出来了。
他莫非改变了注意?也许他不来了,会写一封信来?上面写著什麼:『我们还是不见面比较好,永远祝福你!』之类的话,像那些文艺小说中写的一样。他很可能会写这一类的信的。他是个很能为别人著想的人,他既然知道了一切,当然他会有一番考虑的。外面传来一阵机器脚踏车的声音,门铃跟著响了。她听得出,这是送『限时专送』的信差来了,她差点儿没跳起来,她的心快碎了。他真的不来了,她所想象的这封信终於来了。这个人,既然不打算来,何必又托人来通知呢难道真是这样缘悭一面麼?阿英去开门,把信拿来交给太太。她一看,全是丈夫的信,没有她的,心中宽了一些,随手将信放在茶几上。她心裹又想,也许是下午,他的信总会来的。因篇为,这时候已近中午,他再不来,大概就是不来了。她心想,如果看到那样的信,也就心死了,像这样待下去,非得神经病不可。她的眼睛注视天花板,又从天花板回到墙上,最後停在大女完高中毕业时的相片上面。那天真嫣憨,那艳美如花的容貌,简直就是她的化身。她很安慰,但是也觉得无限的感慨。她轻轻地叹气,直到道一分钟,她才真正如梦初醒,发现自己老了。头发虽未白,可是,毕竟是青春不再了。整个早上,她都以为细心的打扮可以多少恢复当年的风韵,现在,近午的强烈阳光射了进来,即使从镜框的玻璃上,也可以看见自己的衰老样子。她同时又想到许多别的问题,大多数都是关於孩子们的事。幸而祖义并不是真的要来,如果来了,多尴尬呢?还有,他是否变得一如自己想像那样?抑或是很苍老?还有,如果给大女儿碰见了,应该怎样说呢?那丫头什麼都懂,而且似乎有了男朋友了。门铃又响了,她喊声阿英。阿英很不高兴,嘟嘟囔囔的跑去开门。她不再紧张了,她相信祖义是不会再来大了。她知道他也会有同样的心境和考虑,彼此毕竟不再是年轻了,那种傻里傻气的热情的事,他大概是不会再做的。他一定是不会来了。这样也好!她心里想。阿英拿了一张名片跑进来:『太太,有个客人找你!』她接过名片一看:『 祖义』,她差点昏过去。『他……他呢?』她慌慌张张地问下女。『在门口,』阿英说:『 我不认识他,没有见过,不敢让他进来。』她觉得心脏好像要跳出口腔,她觉得全身都要瘫痪了,冰冷了,呼吸也好像停止了。好半天,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中说悲不是悲,说喜不是喜,喉咙哽哽咽咽的。『他终於还是来了!』她心中在说:『终於来了!』『 太太!要不要请他进来坐?』 阿英在等她吩咐。她扶著沙发的背,望望大门那边,可没有看见什麼,只见一部小小计程车的前半部,人呢,被大门遮住了。『 好吧!就他进来好了!』 她软弱地说。阿英还没有转身,却又立刻给她喊了回来。『 不!阿英!』 她说:『你去告诉他,说我不在家!』阿英愕然地望着女主人,『他问我太太在不在家,我已经说了在家!』『没关系!』她坚持地说:『去告诉他,说你讲错了,你在厨房,不知道太太在不在家,进来看看才知道不在!』阿英觉得女主人的态度很奇怪,脸色很苍白,但是还是照着吩咐,到门前去同覆客人。话一说出口,她又後悔起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对不起!先生。』 她听见阿英在门口说:『 太太不在家,刚才是我弄错了!』『 啊?』 她听见一个熟悉的,低沉的男性声音。『真的是不在家嘛!』阿英的声音:『 我不骗你!』经过了一阵短短的沉默,那低沉的声音说话了:『 好吧!请你告拆太太,就说――我问侯她好了!』 那声音听起来,一如当年,富有诱惑力,只是稍微有些沙哑。这一刹那间,她差点儿控制不住自己,差点儿奔出去。可是她毕竟战胜了自己,她紧咬著脣,听见小汽车发动,听见车门呯的一声关上,『 呼』 的一声以後,巷子又恢复了平静。她没有追到窗前去看,要看是可以看得见他的。她的紧张已经成为过去,她飘飘荡荡地走进卧室,就像玉山崩倒般地,颓然地倒在床上。『这样子,很好!』她自言自语地说。她知道,他不会再来了,她能听见他,他当然也听见她。她知道,他是会了解她的,而且,彼此的印象中,将会永速是当年那种美好的青春的模样,永速不会凋零,永速不会再改变。可是,她却禁不住伏在床上痛哭起来。『 阿英,』她哭够以後,喊下女:『 等一会儿你去置些豆瓣酱日来,要买好的,我要亲自弄个炸酱,先生晚上要同来吃阪的,他最喜欢吃炸酱面,我好久没做了!还有,阿英,那个鸭子不炖了,你拿到巷子口那家广东烧腊店叫他们代烤一下,老大老二最爱吃广东烤鸭。对了!再买点儿叉烧,给他们带便当。』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