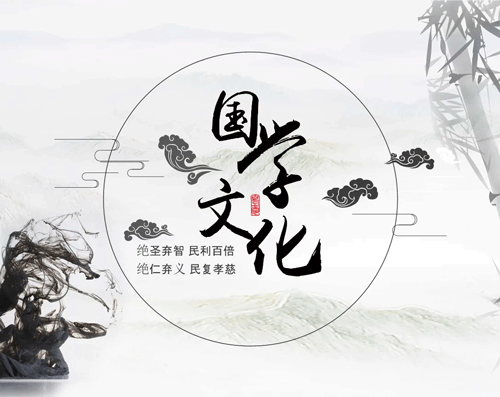神圣与死亡
发布时间:2023-10-16 11:36:39作者:药师网神圣与死亡
释昭慧
死 亡,是每一个生命都不得不面对的结局,而且伴随着死前病苦的折腾,对自己生命的眷恋,对相关人事物的不舍,以及对死后状况杳冥难知的忧惧,人们大都怖畏死亡。怖畏死亡,当然就会寻求添寿、长生或永生之道。于是,宗教就成为人们面对死亡时最大的慰藉了。也许可以这么说:每一种宗教都是一种“面对死亡”的生命哲学。
大体而言,世间宗教面对死亡的威胁,有的是应许人透过祈禳仪式以消灾添寿,有的是应许人透过修仙炼以长生不老,更有的是应许人透过信靠上主以永生天界。佛陀则直接表明:有生无不死,欲“不死”者除非能在根源上“不生”;他教人逆向思考“生”的荒谬性(理智方面的无明、情意方面的我爱,以及伴随而来的种种痛苦),以趋入“无生”(涅槃)为面对死亡的究极之道。
90.06.24 昭慧法师参加辅大“废除死刑国际研讨会”并发表〈废除死刑之佛法观点)
总之,人为力量之所以从来无法彻底歼灭宗教,原因就在于:不是宗教需要人,而是人需要宗教。人们需要宗教,以帮助其面对生命中的大敌——死亡;宗教各有一套自成逻辑的说词,让人燃起一丝希望,期待死亡时得以避免沉沦,获致超升。于是不但亡者减低了面对死亡的哀凄与慌乱,生者也得以缩短“疗伤止痛”的时程。

死亡让人体认到生命的卑微,而宗教却因其教人“面对死亡”,而益发凸显其神圣。显然宗教是如此善意地教人掌握命运之舵,以期摆脱卑微!然而自认为卑微的生命,一旦会遇了他所自认为神圣的宗教,终究很难摆脱那种全身全心依赖信靠,死生以之的情愫;所以宗教的神圣性一旦被侵犯了,会让人产生一种“生不如死”的痛切感,而带给人“面对死亡”时无与伦比的勇气。你很难以常情想像:古今中外那些前仆后继的殉教者,他们面对着凶猛的野兽、残酷的刑罚与锐利的武器,是如何克服对死亡之本能畏惧的!其实他们的思维逻辑很简单:宗教,不但等于,而且大于个人的生命;以极卑微之生命,捍卫那极神圣之宗教,这是“重于泰山”的死亡之道。
神圣的宗教教人如何无惧而尊严地面对死亡,罪恶的战争则强制人们悲惨地大量死亡。这两者,本是背道而驰的两股力量——前者教人“向上提升”,后者令人“向下沉沦”;但当两者被结合而成“圣战”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极其“恐怖”的效果。因为,不但“恐怖份子”本身受到“神圣”的应许而无惧于死亡,而且他们还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种夹带着神圣因素的死亡,能够“早死早超生”;或者可以作如是观:这是建立“神圣国度”的必要之恶。此时宗教徒所培养出来“面对死亡”的勇气,就不止于用在宗教迫害发生时被动的“殉教”行为,而可扩而充之用以“宣教”,甚至不惜为了宣教而侵犯异己,屠戮无辜。
杀人者只要不畏死,他就可以找到无数侵犯异己,屠戮无辜的机会,此所以“圣战”远比任何一种战争都来得“恐怖”。他们坚信:为了神圣而无惧于死亡,会使人更接近神圣。以极卑微换得极神圣,这当然是一场值得豪赌的命运游戏!至此,人类终极的依靠,生命永恒的慰藉,吊诡地形成了苍生重大的浩劫!
90.09.10 昭慧法师参加卫生署疾病管制局“生命有限,大爱无限”记者会
杭亭顿说: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终将一战。此一预言,难道已在九一一世贸中心与五角大厦数千冤魂的身上,得到了初步的见证吗?阿富汗政权不愿交出九一一惨案嫌疑首脑宾拉登,甚至不惜为此而掀起一场血腥的圣战。宗教,难道必须历经无数“死亡”的血祭,才能证明其“神圣”吗?
被视为“神圣”的不只是宗教,人间的意识形态,只要被推到极致(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是父权思想、族歧视、阶级意识还是人类沙文主义),就很难逃脱被神圣化的命运。不可思议的是:世俗人事,只要一经神圣化,同样是如此地贴近死亡!
纳粹把自种族神圣化,相对地就把异族类妖魔化,导致令人发指的灭种大屠杀。毛泽东说他死后要去“见马克思”;马克斯因其创说共产主义而被视同神圣(此所以共产党员可以不需要宗教,因为共产主义早已神圣化而等同于宗教了),正因共产主义如此神圣,不符主义规格的人事物,岂不就等同于邪恶了?于是数以千万计人民同样被妖魔化,而在各种斗争与困顿中悲惨死亡。中国的大一统意识,使得原属政治层面的领土或主权问题,也被化约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信念,台湾人民,也就因为此一政治议题的“神圣”,而长期生活在战争与“死亡”的阴影中。
神圣,令人撩起无限向往,也令人绝望到几乎窒息,只因为它是如此地贴近着死亡!
九十年九月十八日 于尊悔楼
——刊于九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自由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