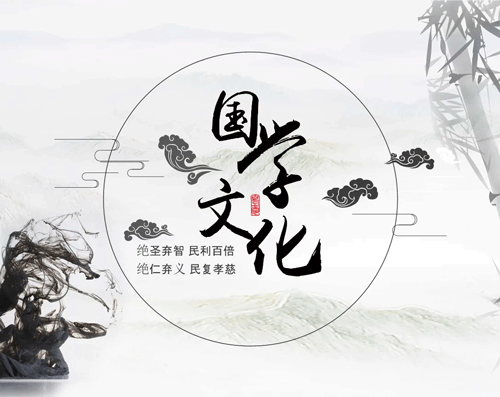禅与企业管理
发布时间:2023-11-23 12:15:24作者:药师网
(2003年11月22日)
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各位交流一下我对禅的粗浅理解与认识。跟企业界的朋友系统交流学禅的体会,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希望这次交流能给各位日后的企业管理工作带来一些启发。
禅坐的禅与禅宗的禅
禅宗的“禅”和“禅坐”的“禅”,虽然有联系,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下面我要跟各位交流的,是禅宗的禅。
“禅”,全称“禅那”,为梵语 Dhyana的音译,汉语的意思是静虑、思维修。这两个词揭示了禅的内涵。生活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在完成觉悟以前,曾经历过相当长时间的禅修探索。早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古代印度人在禅定方面就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禅修经验和方法。据记载,释迦牟尼佛在觉悟以前,曾经向两位佛教以外的老师学习过禅定,而且达到了非常高深的境界,后来觉得不究竟,不能从根本上摆脱生死轮回,就放弃了,重新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深入禅观,最后终于获得了对宇宙人生的领悟。释迦牟尼佛所创的禅观,包括古代印度人一些传统的禅修方法,今天仍然被人们广泛运用着。当然,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人其实也有自己的禅坐传统。
释迦牟尼佛禅观的思想,从“禅那”[静虑]这个词来说,由“静”和“虑”两个层面构成。第一层面指的是心灵的专注能力,梵语音译叫“三摩地”,汉语里“三昧”这个词,就是对“三摩地”的略称。第二个层面指的是心灵对于事物的清晰透彻的认识能力,梵语叫“毗婆舍那”,就是“观”的意思。“禅那”这两个层面的含义,在中国传统佛教的文献里简称“止”和“观”。专注就是“止”,清晰、明了、透彻就是“观”。这两种素质统一起来,就叫“禅”。
止与观的关系,好比被点燃的蜡烛与烛光一样。蜡烛如果老是晃动,烛光就闪烁不定,照东西就不清楚,所以,它一定要保持稳定性。这个稳定性,就相当于心灵的“止”,即专注能力。另外,烛光还要有一定的亮度,如果不够明亮或太昏暗,也照不清楚东西。烛光的亮度就相当于心灵的“观”,即清晰地观察事物的能力。心灵的这两种能力——止和观,在每一个有情生命的身上都存在着。禅坐的目的,就是要用特定的方法把这两种能力加以系统地训练,使之提高。
佛教有不少经论,详细具体地描述了不同层次的生命形态在心灵专注能力和观照能力方面的高低、粗细层次之不同。生命层次越高,专注力和观照力相应地也越强大、越微细。同一个层次的生命形态,每一个个体在专注力和觉照力方面的差异也是非常巨大的。
就人类来说,每个人的心灵专注能力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人专注能力非常强,而有的人专注能力却非常差。一个人如果他的注意力没办法集中,连短时间的集中也做不到,那就说明他的心灵有问题。一个人如果心灵非常专注,那么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以及生活质量就会超过一般人。另外,从人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来看,有一些工作需要有很高的专注能力,比如说,做脑外科手术的医生,当他把一个人的脑袋打开,在里边做手术,那就需要专注能力非常强,不可以有其他杂念。次之,如乡下的妇女绣花,心里也要非常专一,要不然就会绣错了或把针扎在自己的手上。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地方都需要专注。没有专注,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总而言之,专注的深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
人们不仅在“止”的方面存在着差异性,就观的能力[透彻地认识事物的能力]而言,也同样存在着差异性。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生活境界、不同的教育修养、不同的生活阅历,导致人们在认识事物、领悟事物方面的透彻能力也不一样。
止和观是佛教禅修最核心的内容,也可以说是佛教认识宇宙人生的根本方法。经常有人问我,佛教与自然科学有什么区别,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如哲学、心理学有什么区别。区别当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却是方法上的差异。佛法也要认识宇宙人生,但是,它的认识方法与科学是不一样的。科学是建立在感官的基础上,通过对感官所收集的外部信息资料进行归纳、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而佛教认识宇宙人生的方法却是止观,也就是禅坐,通过止观来认识世界,认识宇宙人生。止观的运作,重在对自我内心世界的认识。所以佛教认识宇宙人生,首先是认识“能认识的主体”。能够产生思想感情并作出概念判断的心,就是所谓的“能”。先认识“能”,然后再由此延伸扩展开来。这就是佛教认识事物的根本出发点。
以上我们从语义学角度解释了“禅”的内涵。简而言之,禅就是指心灵的止和观两种能力。佛教有一套非常完备、非常精密的禅修理论,在佛教“三学”[戒定慧]中称为“定学”,旨在帮助人们系统训练和提高这两种能力。
禅宗的禅,与我们上面讲的修习止观的禅坐以及英语里讲的Meditation[汉译为“冥想”],在理念和方法上并不完全一样。它和坐禅、止观有联系,但是也有区别。谈到禅宗的特点,人们都用“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句话来描述。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是我们东方文化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史上最璀璨的瑰宝。
禅是中国化的佛教
禅作为佛之心法,它的真正兴起是在中国。在具体讲述禅的内涵之前,我们先追溯一下中国禅宗的演化历史。
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现在学者通常认为是在公元前 2年,也就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到现在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西汉到隋唐,佛教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将近一千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的祖师们翻译经典,研究教义,阐述佛经的思想,对印度传过来的佛教经典、宗派思想及修行方法,进行了取舍选择、创造发挥,最后在隋唐时期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宗派。
佛教从印度传到东南亚、传到中国汉地、传到西藏,它所面临的文化环境并不一样。在东南亚地区,像现在的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这些地方,佛教传入以前,基本上处于未开化时期,社会文明很不完备,缺乏成熟的信仰,有的地方甚至连文字都没有。所以佛教传入东南亚以后,很快就成为他们文化的主流,一直到现在,现在东南亚有很多国家仍是佛教国家。佛教传入汉地则不一样。那个时候中国的文明已经非常成熟了,有非常完备的社会典章制度,出现过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如老庄孔孟等,哲学思维非常发达,至于语言文字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佛教到汉地来,它所面临的环境,跟西藏、东南亚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认识和接受,一开始就是以中国本有的文化传统为基础的,是一个不断吸收、取舍、创造的过程,而不是完全照搬。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祖师们的不断消化、吸收、创造,到隋唐的时候终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净土宗。在这些宗派里,最能代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完美结合、也就是说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就是禅宗。
禅宗作为一个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派,并不是中国祖师创造和发明的。在佛法的传承上,它有印度佛教的渊源。禅宗在印度的起源有一个非常优美的故事。宋朝的时候,大政治家王安石在皇宫里读到一本佛经,里面记载了这个故事。因为在其他佛经里人们没有看到这个故事,所以有的人就怀疑这是杜撰。但是,王安石是在宋朝皇宫收藏的佛经里面读到的,说明这个故事在佛经里是有根据的。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灵鹫山准备讲法,当时有人供养了他一枝莲花。大众集合了以后,释迦牟尼佛并不像以前那样开始就讲,或者是有人提问然后开讲。他拿着那朵莲花不说话。佛陀这个与平时不一样的表现,使当时所有在会的人感到非常疑惑。这是什么意思?只有一个叫迦叶的出家人——他在佛的弟子中资格最老,岁数也比较大,修行很刻苦——在大众中破颜微笑,也就是说,只有他明白佛所说的法,于是佛陀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在禅宗史上,这句话非常有名。后来有很多禅宗修行人经常问:佛当时传给迦叶的是什么法?这就是禅宗的源头。此后迦叶尊者成为禅法在佛之后的第一位印度祖师,从他开始,一直传到菩提达摩。菩提达摩是印度的第二十八位祖师,在中国则被尊为禅宗初祖。
达摩祖师是在南北朝时来中国的。那时正是南朝的梁武帝当政。梁武帝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菩萨皇帝,他曾经几次舍身出家,还经常在皇宫里讲经说法,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梁武帝听说达摩到中国来,从广州登陆,于是派广州刺史萧昂[相当于广州市的市长]把他请到南京。见面时,梁武帝向达摩祖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修了很多寺院,印了很多经,也经常讲经,也曾经出家,我这样修行有没有功德呢?达摩祖师说,没有功德。梁武帝提问的时候,他是有一种期待,希望能从达摩祖师那里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得到一个奖励性的回答,但是对方却回答说没有功德。因为话不投机,达摩祖师后来便离开了南京,“一苇渡江”——踩在一枝芦苇上渡过长江,来到北朝的河南嵩山少林寺,在那里面壁静坐。河南洛阳一带的人都称他“壁观婆罗门”。
在少林寺面壁静坐了九年之后,达摩祖师终于等到一个法的传人,叫慧可。慧可是中国禅宗的二祖。慧可在出家以前有非常良好的文化素养,对老庄和儒家都有很深的研究,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里的精英。后来他出家学佛,学习坐禅,但是觉得自己还没有通达禅的奥秘。他的剃度师于是介绍他到少林寺去见达摩祖师。慧可开始见达摩祖师的时候,祖师只顾自己打坐,根本不理睬他。为了表达自己求法的至诚心,一天晚上下雪的时候,他一直站在达摩祖师打坐的洞外,雪一直积到他的腰间,他也不肯走。于是达摩祖师就问他,你站在那里想干什么?
慧可说,我想求法。达摩祖师就说,妙法不是以轻心慢心可以求得的,过去的佛菩萨、历代祖师都是舍生命求法。慧可听他这样讲,就拔出刀把左臂砍断,以示求法之诚。现在少林寺还有一个“沥血亭”,就是二祖慧可当年断臂求法沥血的地方。祖师被他感动了,就说,你有什么事情啊?慧可说,我求师父给我安心。祖师说,你找一找你的心,找出来我给你安。慧可沉默了良久,说:“觅心了不可得。”达摩说,我已给你安心竟。找不到心这就行了,也就不存在安与不安的问题了。在这一出其不意的回答之下,慧可开悟了。后来禅宗从慧可传到三祖、四祖,一直传到六祖。
达摩祖师虽然被尊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但是在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禅宗、使之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主流、并对传统主流文化形成冲击的过程中,六祖慧能大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慧能大师在禅宗史上占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可以说,禅宗真正的创始人是他。
慧能大师祖籍河北涿州,出生于广东。他父亲因做官犯错误被贬到了广东岭南,六祖就出生在那里。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他只好以砍柴为生,供养他的母亲。有一天,他将柴送到街上的一家店铺里,恰巧听到有人诵《金刚经》,经中有一句话,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恍然大悟,就问诵经的人,你是从哪里得到这本经的?诵经的人说,在湖北黄梅,有位弘忍大师住在东山,给我们讲法,叫我们诵《金刚经》,说是可以明心见性。六祖听了很高兴,回家把他母亲安置好以后,就离开广东,到湖北去拜见弘忍大师。弘忍大师所住持的道场后来就叫五祖寺。五祖寺就是慧能大师第一次见到弘忍大师的地方。
五祖见到慧能,就问他说,你来做什么?慧能说,为了成佛。慧能大师是一个砍柴的,文化并不高,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教理,当五祖问他来干什么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成佛,这个回答是非常敢于承担的,非常有气魄。五祖听了,就说,你一个岭南人[岭南位于广东,唐朝时还没有开化,属于边地,当时犯错误的人就被贬到那里,是蛮荒之地],一个“獦獠”[“獦獠”相当于“野蛮人”],连开化都没有,还想成佛!六祖说: “人有南北,佛性没有南北。”五祖当时听了,觉得这个回答很不错,但是表面上却不吭声,叫他到寺院后面的碓屋里给大众舂米。
过了一段时间,五祖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要找一个合适的人传法,于是他放话说,现在我岁数大了,你们跟我学法的时间也不短了,大家都把自己的体会用一首诗写出来,让我看看,合格的把衣钵传给你们。这个话传出去以后,在寺院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寺院的首座叫神秀,文化修养很高,修行很好,德行也很好,平时是寺院僧众的老师。大家就议论说,五祖的衣钵非神秀大师莫属。神秀大师也知道大家有这种期许,于是就写了一首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是他对修行的理解。大家可以看出,神秀大师对修行的理解里,有生和死的对立,有身和心的对立,有染和净的对立。大家都觉得这个偈子写得很好,于是不断地传诵。六祖听到这个偈子以后,认为这个偈子写得不好,没有达到开悟的境界,于是就说,我也有一首偈子。他不会写字,就找人来写:“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首偈子是针对神秀大师的偈子写的,它把禅的精神表达出来了。禅是超越对立的,超越身和心、染和净、拂拭和不拂拭的对立,本来就没有染和净,什么地方还会染上尘埃呢?五祖看到这首偈子以后,就把衣钵传给了他。
离开五祖之后,六祖经过了 13年的隐居生活,后来在广东光孝寺出家、受戒,又在南华寺讲法,当时的人把他讲的法记录整理成文,就是现在的《六祖坛经》。我们都知道,佛经一般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而在中国佛教史上,六祖慧能大师的语录《六祖坛经》是唯一一本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但仍然被称作“经”的著作。它是中国祖师向印度祖师学习、领悟了禅的精髓以后,用本土化、生活化的语言[在唐朝来说它是白话]来表达禅的精神、禅的境界、禅的修学的特殊著作。我们说六祖大师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出身樵夫,是个文盲,因为他的生活最贴近普通的劳苦大众,所以他的教法是大众化的,他提倡的修行也是大众化的。《坛经》里讲,“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修行不一定非要出家,“若论修行,在家亦得”。我们的自性每天都在起作用,穿衣、吃饭、睡觉,言行举止,起心动念,都是在用这个心。如果能觉悟这个心,直下就可以成佛。《六祖坛经》把禅的生活化风格以及直指人心、直截了当的做派表露无遗。
六祖以后,中国的禅宗蔚然成风,不仅成为佛教的主流,而且也冲击着主流文化,影响到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宋明理学的复兴,完全是受了佛教的影响,特别是受禅的影响。不少宋明理学家都跟禅师有过交往,从禅师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或者有所开悟,最后表述为儒学的语言,即宋明理学。中国的书法、绘画,在唐宋以后也受禅的影响。可以说整个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生活,无不受到禅的影响。中国文化像一条龙一样,点了“睛”即可以飞升,而正是禅为中国文化点了“睛”。
禅宗的特色
那么,究竟什么是禅呢?用佛教的语言讲,禅是般若智慧——“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禅就是大智慧,大智慧的境界和达到此境界的方法。这样讲,有人会提出疑问:难道佛教的其他宗派修的就不是智慧吗?难道其他宗派的修行就不以开发智慧为目的吗?实际上,其他宗派的修行也离不开智慧,也是以开发智慧为目的。禅宗与其他宗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禅强调在当下开发般若智慧,禅的般若智慧是活泼泼的。
佛教里有一个词,叫“宗教”,它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宗教”含义不一样。在佛教的传承里,“宗”和“教”是分开来讲的,是两个概念,代表两种不同的修行方向、不同的修行风格。释迦牟尼佛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他一生教了很多修行方法,这些修行方法都是针对学生的不同根器而设的,循循善诱,有次第,我们称之为“教”。在这诸多的方法之外,还有一个方法,是专门针对少数上根利器的人而设的,叫做“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们称之为“宗”。
教就是理论,通过理论的学习,逐步升进,逐步训练,逐步提高。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科班性质,按照教科书一步一步地训练,一步一步地达到,这叫教。像天台、华严、唯识等其他宗派,都可以称作教。教的修行,先要有理论的准备、理论的学习和思考,然后再按照理论一步一步地去做,慢慢地超越理论,到最后,不需要理论。
我们可以对宗和教作个比较。教,是通过理论逐步升进,它是一个次第法,它是未来时。而宗则是心法,超越理论和次第,直指人心,直指当下,它是现在进行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没有一刻停止过,就在我们说话的当下,生命正在进行着。每个人都有佛性,每个人都有与佛一样的智慧,这个佛性和智慧没有一刻停止过作用。凡夫和圣贤的区别,只在于有没有发掘这种智慧,有没有认识到这个佛性、开发和利用这个佛性。我们说“宗是现在进行时”,意思是说,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有机会认识佛性,都有机会开发我们本有的智慧。这是禅宗的特点。
“直指人心 ”的“直指 ”,就是我刚才讲的 “现在进行时”。我在讲话的时候,你们听得清清楚楚,就在这每一个当下、每一秒钟中,你们的生命都没有停止过,实际上,就在这每一个现在进行时中,你们已经当下在用自己的佛性,你们完全可以当下认识自己的心性,而且这个当下的体认,甚至不依赖于理论,不依赖于科班式的教学,它是直接的。
“宗”这个方法,是不立文字的,换句话来说,它是在语言文字之外,通过心与心之间的直接契合来完成的。禅宗之法又叫“心法”,这个心法不在文字当中,只能在当下的心地上去实证它。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代替实证,也无法传达这个心法。
由于禅宗的心法比较难理解,所以在禅宗语录里,古代祖师用了很多善巧方便来描述禅的特色。宋朝时,有一位五祖法演禅师,他讲了一个故事,记录在一本叫《宗门武库》的书里。这个故事我觉得是他杜撰的,但是它确实把禅的特色讲出来了。五祖法演禅师给我们讲,禅的教法有什么特色呢?他打了一个比喻,说有一家人以做贼为生,贼父亲经常带着贼儿子到外边偷东西。我们知道,三十六行,行行有门道,偷东西也有偷东西的门道。儿子很快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做盗贼应该掌握的技巧。有一天父亲对儿子说,“我老了,干不动了,以后的事你得接班。”儿子说,“我跟你这么多年,基本的东西我已经学到手了,现在要交接班了,你得把你最核心、最尖端的那一招教给我。”父亲说,“行,今天晚上教给你。”于是,那天晚上贼父亲带着贼儿子,来到一户人家的院墙外,先把墙掏了一个洞,进到院子里,接着又潜入一个房间,撬了锁,这些都是常规的,贼儿子觉得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经常这样做。接着,他们来到主人的内室,柜子内满是金银细软。等把柜子撬开后,贼父亲就示意贼儿子跳进去。儿子进去以后,这个贼父亲突然“啪嚓”一下把柜子门锁上了,然后就往外跑,边跑边喊:“有贼啊,有贼啊!”宅子里的人都被惊动了,然后贼父亲一个人跑掉了。这家人起来到处找,也没有发现丢了什么东西,闹嚷了一顿,都接着睡觉去了。贼儿子在柜子里这个着急啊,因为他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没有学到解决的办法。就在他无计可施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办法。他用手不断地抠这个衣柜,听起来就像是有一只老鼠在里面啃东西一样。主人躺下以后,听到柜子里有老鼠,就让仆人点枝蜡烛把柜门打开看看。柜门一打开,贼儿子突然“噗”地一口把蜡烛吹灭,跳出来,一下子蹿到了外边。跑到院墙边,他就心里开始叫苦。原来掏开的那个洞口,已经被他父亲用蒺藜[像铁丝网一样的东西]给堵死了。后面的人追来了,贼儿子急中生智,把旁边的一个尿筒套在自己头上,从满是蒺藜的洞里爬了出来。跑出来以后,贼儿子气喘吁吁地回到家中,开始埋怨父亲。他父亲却回答说,“你不是要我教给你最尖端的东西吗?我今天传给你了。”这就是心法。
大家想一想,这个心法是什么呢?当我们的心在没有任何依靠、没有任何理论可凭借的情况下,陷入一种类似于绝境的状态,而后天所学得的种种知识、观念、习惯性的思维,乃至情绪反应等等,全然无效,不得不放下,这个时候,我们心里本有的智慧就会自然而然地生起。这个就是心法。在这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执著和依靠的状态下,我们的心往往能解决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当我们的心彻底摆脱了一切理论知见、思维习惯、一切套路的束缚之后,它是空灵的,具有无限创造的可能性。不像教下那样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完成这个步骤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下一步又是什么效果,这是教的做法,而宗门中全然没有这些东西。
与佛教的其他宗派相比较,禅宗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理论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这一特点决定了禅的传播特别注重师承,重视以心传心。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迦叶尊者破颜微笑,法的传承就是在无言之中完成的。从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给迦叶尊者传法开始,一直到今天,禅的传承没有中断过。以我所属的临济宗来说,现在传到了 45代,如果从释迦牟尼佛算起,已经是 85代了。在世界文化传播史上,像禅宗这样,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一代人跟下一代人,代代没有中断过,这是很少见的。这种传承方式,是人类文化传承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中国佛教史上,国家虽然经历过许多苦难,包括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个传承的源流没有中断过。六祖以后,中国的禅宗呈遍地开花之势,形成五个宗派——沩仰宗、曹洞宗、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一花开五叶。这五个宗派都产生于中国的唐五代之间。传到今天,最有影响力的有两个宗派,即临济宗、曹洞宗,其他的宗派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在临济宗、曹洞宗这两个宗派里,更有影响的是临济宗,所谓“临济子孙遍天下”。当年临济义玄禅师在江西得法以后,来到河北正定传法。所以,临济宗的发祥地就在正定的临济寺,它是临济宗的祖庭。
前边我讲了,禅是一种心地法门,在这里,语言文字没有用,它的修证境界亦非语言所能描述,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既然是这样,那么如何才能确定所达到的境界是不是对的呢?师承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一个人在承传法脉之前,必须经过某位大成就者的印证,证明确实开悟了才行。从释迦牟尼佛印证迦叶尊者开始,一代一代地印证,一代一代地承传,禅宗的法脉就是这样被继承下来的。历史上,凡是经过印可的禅师,从修行上说,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一个开悟者,在修行的过程中,要寻师访道、广参博学,要经过很多有修行的人的印证才行。虽然在修证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经教来印证自己,看自己的所修所证是不是与经书上讲的相吻合,但是最稳妥的还是通过开悟的老师来印证。
禅宗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见性成佛”。“见性成佛”的“性”是什么呢?就是佛性,就是我们本有的、无住的、平等的、清净的、无碍的觉性。我们日常的举手投足、起心动念、待人接物,都是佛性的作用。佛性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只是我们很少回光返照它,这就叫“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所说的成佛,就是要成就“自性佛”,即体证这个无住平等、清净无碍的觉性。另外,性也可以说是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宇宙人生的差别性,认识到它的统一性,我们就算抓住了打开宇宙人生奥秘之门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我们就可以成佛。
禅者开发心灵的方法
禅的精髓在于心灵的开发,即开发我们心灵中本具的佛性和本有的智慧。
也许有人会问:开悟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以我来说,我没有开悟;即使是真的开了悟,恐怕这种境界也无法说出来与人分享。在这里,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借助古代祖师的修道悟道经验,来描述一下禅的悟境。我们可以根据过去祖师和现在的修行人的心灵状态、生活态度和修行历程,从这些角度来了解一下开悟的境界。
根据古人悟道的经历,关于开发心灵智慧、开启佛性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三个阶次,也可以说是三种方法。
禅者开发心灵的第一个方法,叫“大死一番”。
我们这里所说的禅者,不仅指出家的禅者,同时也包括在家修禅的人。从古到今,有很多在家的修禅人。在唐代,有不少村夫愚妇没有什么文化,也能拥有禅的悟境。禅宗典籍上记载了不少老太婆把那些禅师问得哑口无言,答不上来。在宋朝,也有很多读书人修禅,如苏东坡、黄庭坚、王安石等等,他们都是在家人。近现代在家修禅的人也很多。所以我说禅者包括在家和出家。
前面讲到,佛教所说的般若智慧不在语言文字上,它是每个人内心本具的一种品质。我们的心每时每刻都在活动,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应,这个主宰生命活动的、活泼泼的能动的心,它所本具的根本品质,就是般若智慧。一个人的学历高低、贫富差异、阶级地位、高矮胖瘦、男女老幼,这种种的一切,不是心地的品质,而是后天的现象。这一切不仅与心地的品质没有直接联系,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后天的差别现象,包括我们所学到的知识、观点、结论,有时反而会障碍本具的品质。当然,与生俱来的劣根性,如贪心、嗔恨心、自我中心意识、偏执等等,更是我们本具品质开显的巨大障碍。
所以想要认识本具的佛性,开发这个品质,就必须“返本还源”。返本还源不是在外面去追求一种神秘的东西,而是在内心里面去发现。我们越是向外寻求,离内心本具的品质距离就越远,所以古人讲“转求转远”。要想把内心本具的佛性品质开发出来,必须把后天的分别心、妄念、情绪、观点全部放下,也就是说,要从那些先入为主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贪嗔痴等种种束缚中跳出来。放下它们不是说要把我们变成白痴,不是说要我们把所写的论文烧掉,而是要把我们的心从对这些东西的执著,包括对财富、地位、生死、色相等等的贪著中解放出来。这个问题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解决的核心问题。
每个人的生命意识之流,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我们只有透过这个意识之流、妄想之流,才可以见到内心本具的佛性。那么,怎样才能透过这个意识之流呢?这就是我所讲的要“大死一番”,也就是古代禅师讲的“截断众流”。在浩浩荡荡的长江上修一座堤坝截住江流,是非常惊险的,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思想、情绪、念头从来就是滚滚向前,没有停过,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它们的空性,妄以为它们是实有的,于是错误地想:啊!这是我,我的思想,我的感觉,我的观点,我的看法,总而言之是我。其实它只是一个意识之流,生命之流。这好比电影,我们觉得整个故事很完整,其实那只不过是由一大堆静止的图像组合出来的,只是通过电影胶片连续投射,在视觉上给我们一种连续的动感而已。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生命之流力量非常强大,但是一旦我们截断了它,生命将是另外一番风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描写的正是这种全新的生命境界。这一点可能是今天的人难以理解的。
生命之流被截断,古人称之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语言思维的心走到了绝境,心念的运行停息了下来。生命之流被截断后,并不是生命断灭了、什么也没有,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在起作用。在言语道断、心念灭的地方,心灵本具的般若品质,从来没有中断过,还在那里起作用。我讲话时,你们不需要任何作意就能听见;开水溅到你的手上,你不需要任何作意,马上就能感觉到痛。这当中,是什么东西在听?是什么东西在痛?同样的,当我们思考、产生爱和恨的情绪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在思考?是什么东西在爱?什么东西在恨?是什么东西在指使我们做出种种动作、产生种种意识?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面对过,而且正面对着,我们可以从这里入手来认识禅。禅的任务就是关注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关注我们生命每一天的活动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起支配作用。
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仅只停留在知识层面上的探讨。活着的时候要明白,死的时候也要明白;有钱的时候明白,穷的时候也明白;顺利的时候明白,不顺利的时候也明白;年轻的时候明白,老的时候也明白。这个明白,超越了我们的生老病死,超越了我们的穷通寿夭。这个明白,别人不能代替——像上厕所一样,谁也不能代替。古人讲,“各人吃饭各人饱”,《坛经》里讲“自性自度”、“自性自悟”,自己的问题还得自己去解决。只有自己去领悟,自己才会明白。
“大死一番”的意思是,要透过意识之流,截断它,像三峡大坝截流一样。唐朝有一位香严智闲禅师,本是百丈禅师的弟子,年轻的时候在百丈座下修行,但是没有开悟。百丈禅师座下有很多弟子都开悟了,为什么他没有开悟呢?因为他太聪明。百丈禅师还有一个弟子,叫沩山灵祐。百丈禅师去世后,智闲只好到师兄沩山灵祐那儿去参学。灵祐禅师本来是他的师兄,后来变成了他师父。灵祐知道他的毛病,有一天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听说你在师父那里问一答十,现在你也不用跟在我身边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在你父母生你以前,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一问,他答不上来,只好退下去查经论,翻来翻去,查不到答案,他就又去找沩山禅师,要沩山为他说破。沩山说:“我不给你讲,你应该自己去悟。”过了好长时间,智闲禅师还是不明白,非常失望,说:“我从今以后再也不学佛了,只做个粥饭僧,每天吃饭,什么也不想,免役心神。”后来他来到河南南阳,那儿有一个大禅师——慧忠国师的塔,智闲就在那里守墓。他在那里自己种点地糊口,每天打扫卫生。有一天锄草的时候,他把一个瓦片捡起来,无意中抛到竹子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他突然开悟了。开悟了以后,他回去沐浴更衣,朝着沩山方向烧香礼拜。他说:“和尚大慈,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哪有今天啊!”就是说,如果当时沩山灵祐禅师告诉他一个答案的话,他可能就满足于那个答案,不再在自己的心地上深入了。心地的深入需要放下语言,放下既有的结论,单刀直入,直接去体会。
大家想一想,香严禅师悟在哪里呢?是悟在瓦片敲竹子的声音上吗?如果悟在那上面,那我们每天敲瓦片,为什么不开悟呢?他之所以能开悟,关键是在当他回答不了沩山的问题的时候,他把原来所学的知识、结论都放弃了,让自己一直非常活跃的意识活动止息下来了。他说“此生不学佛法,做一个粥饭僧”,所谓粥饭僧,就是什么事也不管。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的意识活动止息下来的时候,在那个情况下,一个外在因缘的触击,就有可能使我们当下截断意识之流,见到心性的另一种风光。这个过程,叫“大死一番”,即把以前的一切都抛开,全部放下。
禅者开发心灵的第二个方法,叫做“直下承担”。
前面讲过,禅宗的心法与次第禅的止观方法虽然有联系,但本质上不一样。在印度,禅观法门里,像止息观、因缘观等等,都是对治法,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心里有这样的缺陷,所以需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对治它。而中国禅宗的特色是要求禅者全力承担。
全力承担是什么意思呢?即念念相信一切都是佛的化身,一切都是佛性的妙用,在此信心之下,回归于无心而照、照而无心,回归于统一性,包容一切,不取不舍。心里面的善恶念头,外界的环境,大自然中鸟语花香,四季变换,太阳东升西落,月缺月圆,这一切无不是法身。所以祖师讲:法不是见闻觉知,但是法不离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所实践的,就是生命的全部境界。因此谈起全体的承担,就是不外求,不靠外界的力量来拯救我们,当下证真,当下体悟万物的统一性,当下让生命本具的佛性放光。
“正法眼藏”这种说法,是一个比喻。在眼睛没有打开之前,我们生活在黑暗当中。因为没有真正的智慧,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对待的,如是非、美丑、来去、生死等等。只要有是非、美丑、得失、利害之分别对待,我们就生活在矛盾当中,就生活在愚昧昏浊狂乱之中。而禅的境界则是一种统一的境界,就大的方面而言,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空间的统一,自他的统一,人和自然的统一,个人和社会的统一;就个人而言,身和心的统一,言和行的统一。修禅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归这种统一,它是我们心的本原状态。
临济祖师讲:“道流!是你目前用底,与祖佛不别,只么不信,便向外求。莫错!向外无法,内亦不可得。”——这个“现在进行时”,与祖师、与佛没有什么区别。法不用向外觅。如果有内外的对待就不对了。“大丈夫汉,更疑个什么?目前用处更是阿谁?
——这是禅师说话的语气,他逼迫我们当下承认。
“把得使用,莫著名字。”——你认识了它,你就可以使用它。而它没有名字,没有形象,没有方所。“号为玄旨,与么见得,勿嫌底法。”——如果你认识了目前的自己,就是现在正在进行时的这个东西,你就彻底摆脱了生死的缠绕。嫌的意思是嫌弃、抛弃、不要,取舍——我要这个,不要那个,我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如果你认识了它,怎么都好。在家好,出家也好;穷也好,富了也好;健康好,生病也无妨;活着好,死了还好。如果见到了我们生命中现在进行时的那个,我们就可以获得生命的主动权,由被动的生活变成主动的生活;由有选择的生活变成一种欣赏的生活;由发牢骚、抱怨的心变成赞美、赞叹的心,感激的心。
长沙景岑禅师说:“尽十方世界是沙门眼”——十方世界都是智慧,都是出家人的眼;“尽十方世界是沙门全身”——十方世界,天地万物,山川河流,就是我们自己;“尽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十方世界都在自己光明里;“尽十方世界无一人不是自己”——十方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是你自己。所有的对立都统一了。什么叫开悟呢?现在我们可以在语言上勉强下一个结论:开悟就是生命中所有的对立面全部统一起来了。领悟了这个统一性,找到了这个统一性,就获得了生命最大的自在、最大的自由、最大的主动性。迷失的生命在矛盾里,开悟的生命在统一里。我再强调一点,这个统一是在自己心地上的统一。
全体承担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需要训练。怎么训练呢?就在当下所起的这一念上,承担一切原本如是。说到承担,实际上我们是一点也开口不得,完全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内证境界。就像鱼在水里,它不去思考水。为什么?因为它就在水里边。我们本来就在佛性里,本来就在道里,我们的整个活动都在佛性里,内外、主客观的一切都在这里。所以,对于佛性、对于大道,我们是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就,很难说。
有一个公案讲全体承担。宋朝有一位大词人黄庭坚,他是学佛的,据说他知道自己的前世。有一次,他偶然走到一处自己上辈子生活过的地方,看到有一位老太婆在一个灵位前供饭。他走进屋里,觉得非常熟悉,书、书架,都觉得很眼熟。原来老太婆的女儿已经去世,她就是黄庭坚的前生,所以每当忌日供饭的时候,黄庭坚就不觉得饿。黄庭坚跟晦堂禅师学禅,因为他是个读书人,所以晦堂禅师就用孔子的话来给他讲。晦堂禅师说,《论语》里有一句话,你有没有注意啊?孔子跟弟子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学生们啊,你们以为我在法方面对你们有什么隐藏吗?没有!我从来没有对你们隐藏过任何东西,一切都是现成的。晦堂禅师跟黄庭坚讲,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黄庭坚说,我不明白。晦堂禅师说,那你就好好地参一参吧!于是黄庭坚每天都参这个问题,可是尽管费思索、动脑筋,还是找不到答案。有一天,他陪晦堂禅师在山间散步,正好看到一树桂花怒放。晦堂禅师就问:“你闻到桂花香了吗?”他说:“闻到了。”[在这以前,他一直在想“吾无隐乎尔”是什么意思,请各位注意这个背景。]晦堂禅师马上说:“吾无隐乎尔。”一言之下,黄庭坚开悟了。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全体承担。
禅者开发心灵的第三个方法是“转身向上”。
转身向上是个形象的说法。当我们取得一个进步、获得一个成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执著于那个进步和成果,全身心都系在上面。转身向上的意思是说:放下,往前走。有一首诗:“百尺竿头不动人”——我们到了很高的境界,在百尺高的竿头上站着;“虽然得入未为真”——到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究竟。在这里,还需要再往前走一步——“百尺竿头重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禅师们在修行开悟的过程中,心路历程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每个人过去世所积累的经验不一样,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景象也不一样。但不管怎样,这一切都得放下。有一些景象看起来像是开悟,但不是开悟。有一些景象是初浅的悟入,不是彻底的悟。即使是彻底的悟入,一旦我们的心执著于它,那它又有了对立面——悟和不悟的对立。所以,不管出现什么境界,都得无住。如果执著悟,也是错误的,也需要放下。
“转身向上”,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要不断地超越、不断地放下。用老子的话讲,就是“损之又损,至于无为”。把所有达到的不断地放下,不断地放下,不断地放下,将这个心空得没有一点点滞碍。要知道,我们的心中,只要有一点点执著,就会障碍我们的道眼。所以古人说,“金屑虽贵,落眼成翳。”金屑虽然很贵重,但是放到眼睛里面,却会带来毛病。在修行的过程里,在工作、生活的进程里,我们所得到的成绩、得到的境界,如果我们执著于它们,它们就会把我们束缚和障碍住,再也不能前进了。宋朝的大慧宗杲禅师讲,他在修行的过程中,大悟十八次,小悟无数次。绝大多数禅师开发心灵的般若智慧,都不是一步到位的。虽然他的方法是“顿”,但是,修行的过程也是很漫长的,需要经过很多的境界、很多的磨炼,要拐好几个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经常转身向上、经常超越自己。这种精神就是《金刚经》里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们后天的理论、知识、概念,这些先入为主的见解,以及我们先天所具的贪嗔痴慢疑等劣根性,自我中心主义,这一切,我们执著于它们,它们就会成为我们开悟的障碍。连开悟的境界、开悟的感受,我们也不能执著于它,执著也是障碍。可见,问题不在我们执著在什么上面,问题在我们是不是有执著。只要我们有执著,那就是障碍。从这里,我们就能理解临济禅师所讲的“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一般学佛的人看了会很惊讶,怎么能杀佛杀祖呢?这个杀,不是杀戮,而是放下,当我们的心被佛的概念、祖的概念或者被自己所领悟的境界束缚住了,出不来,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放下。所以这个“杀”字,不是拿刀砍,而是放下、放下、不断地放下。
马祖道一禅师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即心即佛”。祖师讲“心即是佛”,其实只是一只船,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彼岸去,但是很多学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执著于“心即是佛”这个结论。有一位大梅禅师,在马祖座下开悟以后,在山里修行,有一天,马祖就派一个人去试探他的境界。被派去的那个人见到大梅禅师,就问他:“如何是佛?”大梅回答说:“即心即佛。”试探他的人说:“你搞错了,现在马祖说法已经变了,现在讲非心非佛。”大梅回答道:“管他非心非佛,我这里依然是即心即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是“即心即佛”还是“非心非佛”,并不重要,关键是你的心是不是住著在一个东西上面,是不是已经得到了自在,有没有从语言、概念、情绪、我见里解脱出来,若是解脱出来了,怎么说都对,“即心即佛”对,“非心非佛”也对,“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对。试探他的人回去后,向马祖报告了这个过程,马祖很高兴,说“梅子熟矣”,认可大梅禅师的修行已经到家了,已经不会再为各种名言、思想和知见所转动了。
可能有人会问,一切都不执著,究竟是什么状况呢?从自受用来说,很难用语言表达;从外在表现来说,就是一个平常。所以真正彻悟的人,他是平常的,不搞特殊,不标新立异,不突出自己,只是平常心。有位大珠慧海禅师,有人问他,你现在这么高的境界了,还修行吗?他说,还修行。怎么修啊?“饥来吃饭困来眠”,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那人又问,我每天也吃饭睡觉,怎么不是修行啊?禅师说,你吃饭的时候,“千般计较”,心里有好多妄想,有很多思想负担,比如你吃饭的时候还在想工作啊、生意啊,想职位啊、工资啊,想家庭啊,分别饭菜的好坏啊!你睡觉的时候呢,更是问题不断,各种思索、计量、盘算,挥也挥不去,剪不断,理还乱。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吃饭和睡觉时的状态。吃饭、睡觉如此,做人做事、接人待物、言谈举止无不是如此,所以我们不自在,很烦恼很累。但是禅师与我们凡夫不一样,他是自在的,因为他在吃饭睡觉时受用他的般若智慧。

智慧是普遍的,真理是普遍的,从来没有停止过作用。打坐时,它在起作用,睡觉时它仍然在起作用。如果睡觉时它不起作用,说明这个道是假的。《中庸》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者,非道也。”所以说,悟道之后,只是平常。平常心是道。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考察了禅者开发内心本具的般若智慧所使用的三个方法,或者说所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大死一番;第二,全体承担;第三,转身向上。我所讲的,只是文字概念,并不是禅宗的心法本身。如果有一位真正的禅师在这里,他会给我一巴掌,因为我的这种讲法,把他们玷污了。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用语言,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分析,这样听众才能有所了解。
禅者的精神风貌
刚才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了禅者开悟以前的修行历程,下面我们拟从禅者开悟以后的精神境界、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角度,也分三个方面来透视一下禅者的精神风貌。
第一,孤峰独宿。这是讲开悟的人,他的心灵独立了,已经摆脱了一般人普遍具有的对外在环境的依赖,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就像是一位隐士,住在高高的山顶,住在凡人不到的地方。他的心在那里,超越了一切法,这就是孤峰独宿。
可能有人会问:禅师他吃不吃饭、喝不喝水啊?他也吃饭,也要喝水,他也需要这些东西来维持体力。但是他的心境是独立的,不像普通人心里依赖很多东西。我们从小到大,接触了很多意识形态、很多价值体系,我们的心依赖这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想,各位不会突然把头剃光了去上班,那样的话,上街坐地铁,肯定会有很多人看我们,到了单位,整个公司的人都会感到很惊讶。其他跟社会舆论不相容的言行,我们就更不敢做了。由此可知,人是有依赖性的。人的依赖多种多样,有情感的依赖、身体的依赖、饮食的依赖、睡眠的依赖、社会舆论的依赖、人际关系的依赖、财产的依赖……如果把这些拿掉了,我们就完蛋了,精神会彻底垮掉了。但是,禅师从所有这些依赖之中解脱出来了。
解脱的人不一定就标新立异,相反,往往会表现得更平常。当然,有时候他也会标新立异,以此来表现他心境的自由。悟者的心境不依赖于一切的概念名言、思维习惯、价值判断,所以有的时候,禅师的言行表现得十分奇特,普通人无法理解。比如问:“什么是道啊?”禅者可能会回答说:“砖头就是道。道在屎尿中。”这样的回答,我们常人接受不了。因为他获得了自在,超越了一切对立,所以一切都是道。我们问他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他可能说是圆的,也可能说是方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怎么回答,而在于他心境的自由。
有位禅师为了表明自己的悟境,头上戴着儒冠,脚上穿着道鞋,身上穿着僧袍,然后出来问大家:我是僧?是儒?是道?
赵州禅师也有类似的行为。有人来拜见他,他明知故问:你见到我了没有?学人说我看到了。赵州禅师说,我是一头驴,你在哪里看到我?我们不要在乎他说他是一头驴,如果把心放在这个上面,就错了。实际上,他这个回答,是想把他从一切依赖和缠缚中解脱出来的自由、超越和独立的境界展示给我们看。
天台德韶禅师有一首诗:“通玄峰顶,不是人间。”饿了还是要吃饭,困了还是要睡觉,怎么不是人间呢?这里的“不是人间”是说,他已经从人世间的依赖、纠缠、执著中跳出来了,拜拜了。“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满目青山无一事。
寒山子是一位很喜欢写诗的禅师,他经常借诗歌来描写心灵独立的境界。“人问寒山道”,他住在寒山,寒山道在哪里?“寒山路不通”,到寒山的路很不好走。“夏天冰未释”,夏天上面还结着冰。“日出雾朦胧”,太阳出来了,仍然雾蒙蒙的。“似我何由届?”既然寒山那么难到,我又为什么能到呢?“与君心不同”,原来道路、气候不是关键,关键在心。“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寒山的路永远是通的,不在于夏天的冰,也不在于冬天的雾,你的心如果和我的心一样,就能到寒山。
药山惟俨禅师有一位在家弟子,名叫李翱,曾经做到户部尚书,是宋明理学在唐朝的先锋,写了一些哲学方面的文章。古代跟现代不一样,如果李翱是现代人,他有什么思想写出来一发表,大家都能查出来他的思想是从寺院来的,是从师父那儿学的。但是古代没有报纸,没有电脑,他天天去亲近禅师,然后写出一本《复性书》。他没讲这是跟禅师学的,所以人们就认为,哎呀!李翱的哲学不得了!其实他是跟出家人学的,盗用我们的品牌。[众笑]他经常去亲近药山惟俨禅师。有一天,药山惟俨禅师在山上散步,忽然见到风吹云开,月亮出来了,大啸一声。这一啸不要紧,结果在澧阳那个地方,方圆九十里地的居民都听到了。第二天大家“迭相推问”,追问到最后,才知道原来是老禅师在山顶大啸。因此李翱就作了一首诗,描写药山惟俨的生活:“选得幽居惬野情”,他在一个人迹不到的地方住。“终年无送亦无迎”,一年到头,不送不迎,这是讲对待客人心不攀缘,不追求,也不等待,心是自在独立的。“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各位看看,这种境界多么美!
禅师的心路,只有和禅师有一样修证境界的人才知道,只有开悟的人才知道,没有开悟的人不知道。按古代禅师所讲,不仅人不知道,就是鬼神也不知道。古人讲,我们起心动念,鬼神是知道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嘛。但是开悟的禅师,他的心路鬼神是觉察不到的。
金碧峰禅师早期修行不太用功,有一天打坐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鬼,拿着一根铁索要套他的脖子,他说:哎!怎么回事?我修行了一辈子,还得跟你走啊?鬼说:阎王让我带你走,已经下了请柬。金碧峰禅师知道自己修行还没有到家,所以阎王找到他了。他就跟鬼商量说:这样吧,你晚点再来,一个礼拜以后再来。鬼走了以后,金碧峰禅师便加紧用功修行,最后开悟了。开悟的人的心在哪里,我们找不到,鬼神也找不到,所以七天以后,那个鬼再来找他,找不到了,天上地下都找不到他的影子。
南泉普愿禅师是一座寺院的方丈,有一天,他到田庄去视察工作,当他走到半路的时候,庄主已经出来迎接他了。他是突然去的,事先没有通知,也没有警车开道,他说:哎!你怎么知道我要来呢?庄主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土地神说,明天南泉普愿禅师要来。南泉禅师说:哎呀,坏啦!我修行不好啊!我动了念头第二天要去哪里,土地神都知道了。
这是讲心灵上的孤峰独宿。下面我们要讲一下孤峰独宿的行藏、行止,也就是表现在外的行为。这种境界更不是普通人所能把握、所能评断的。悟者的所作所为,已经从舆论、意识形态、价值判断里跳出来了,所以,他的发心和行事,有自己的判断。他心里存有宇宙的准则、法界的准则,他是按照心里的准则去做,永远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判断他,绝对会出错、出偏,所以古人讲,证道者是“逆行顺行人莫测”,逆行就是违背常理判断的行为。
济公本来是个出家人。社会上的人喝酒吃肉没关系,但是从出家人的戒律来说,他的表现就是逆行。他既喝酒,又吃肉,哪儿都去,什么人都交往。如果我们从这些外在表现去评判他,就会认为他是坏和尚。佛教作为一个宗教组织,它既存在于社会中,必定会有一套外在的要求和规范。这些规范与要求,必须是与社会兼容的,比如佛教的慈悲和智慧,跟世间的文明就是完全兼容的。但是禅师的心境,在他得到大自由以后,他所表现于外的言行,以外人眼光来看,往往不太容易把握。禅师的心境是独立的,我们不应该用世俗的标准来简单地评判他的是和非。
明朝有一位道衍法师,俗名姚广孝,江苏人。明朝开国皇帝是朱元璋,朱元璋下面是建文帝。建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朱元璋没有把帝位传给儿子,而是传给了孙子。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就不太高兴,想篡夺帝位。燕王与道衍法师关系很好,很谈得来,这个法师很怪,平时不太说话,三角眼,瘦瘦的,曾经有一位相师说他是“饿虎”,意思是说他其貌不扬,但是很有内在的力量。他后来做了朱棣的幕僚。建文帝登基后,朱棣在燕京打出“靖王”的旗号,说建文帝身边有小人,带着军队从燕京打到南京,目的就是要篡夺帝位。参与整个谋划的核心人物就是道衍法师。朱棣得到天下之后,就做了明成祖。明成祖对道衍法师非常尊敬,封他非常尊贵的官,赐给他房宅、美女。但是他很奇怪,他上朝的时候穿官服,回家后穿僧袍,对于赐给他的一切,瞟也不瞟。他回家探亲的时候,家里人都骂他,嫂子见他的面,骂他大逆不道。明成祖刚刚夺得帝位的时候,老百姓都不能接受,因为是篡权的,所以家里人都这样对他。明成祖篡夺帝位,我们暂且不去评价,但是如果深入地了解道衍禅师这个人,包括了解有关他的文献,再观察他一生的行藏,我们是很难轻易给他下结论的。他的心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做,我们也不知道。
还有一个人物——雍正。现在经常放关于雍正的电视剧。这个雍正皇帝,依我看,现在的人完全把他看错了。雍正是一位佛教徒,做皇帝以前他在雍和宫住,雍和宫是他的家宅,当时是叫做雍亲王府。做皇帝以前,他就喜欢修行,喜欢坐禅。他还经常请一些禅师在雍亲王府里打禅七,后来他开悟了,自称“圆明居士”。他曾经对古代禅师的语录作了一番挑选,编了一本《御选语录》。清初的禅宗,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见解,他曾经参与其中,评判是非。如果有哪两派的见解不一样,他就根据自己的判断下诏书,说这一派对、那一派错,很独裁。但是他也说,见解不一样也没有关系,你不同意可以到北京来跟我辩论,辩论赢了,我听你的;辩论输了,你得改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首先是一位佛门居士,然后才是一位皇帝。有很多小道消息,说他篡夺帝位等等,你们肯定都知道,后来又说他是暴君,好色、贪财。其实他是明君,不过他的手段很强硬。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打下江山之后,很多人往往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雍正为了整顿清初的吏治,特别是对皇室的腐败分子,惩治起来决不手软,经常将这些人发配到新疆、东北等地充边,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一路走一路造谣,很多传闻就是这么出来的。现在清朝的文件档案保存得比较完整,雍正时代经过他手批的文书现在都在。经历史学家统计,雍正在位 13年,没有一天休息过,每天必须工作十几个小时,只有这样才可能批完这么多文件。他是个勤政的皇帝。如果我们对他佛教方面的修养不了解,就很容易看错,因为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宇宙万法的原则已经在他的心里了,他那么做自有他的道理,我们凡夫的评价却很容易发生错误。
孤峰独宿,意味着禅师的心深不可测。深不可测不是说他很神秘,而是说他无所住。他已经从普通的世间舆论、甚至从世间认为的善法里跳出来了。《华严经》里讲到,善财童子拜访过很多有修行的人,有出家人,有居士,有暴君。暴君说:我这个暴,有它佛法上的意义。他还拜访妓女,这位做妓女的大菩萨也讲了很多她怎么修行的事儿。所以说禅师的境界,在心境上独立无住,在行止上超出凡情。
第二,立处皆真。这是讲禅师的心已经从好恶的情绪里解脱出来了。普通人生活在爱憎取舍之中,心不能安住在当下。“立处皆真”这句话来自于《临济禅师语录》。临济禅师说:“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到哪里都是主动的。作主不是说主宰一切,而是说他在面对人生的一切逆顺境界时,都是自在、自由的。“立处皆真”,凡所立之处,都跟真理不相违背,言行举止都符合真理。“途中即家舍”,途中就是家。家,作为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在遥远的他方和未来,当处就是,当下就是。任何时候都能体现出生命的最终价值,禅师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他能够安住当下,一切都好,一切都肯接受。
虚云老和尚是开悟的大禅师,对中国近代佛教影响巨大,我的师父曾经做过他的侍者。有人问我师父:你跟虚云老和尚这么多年,他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师父的回答给我的感触很深。我以为他会说某一天发生了某件事,他没有。师父说,虚云老和尚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任何境遇下,都不抱怨,都很自在,一切都是好。在云门事变中,虚云老和尚被别人围攻毒打,他没有任何怨言;在他一百多岁的时候,还去修庙,很投入,很自在,他永远住在那种平和的心态里面,没有说这个好那个不好、 这个要那个不要,没有说现在自己很糟糕,他没有抱怨。
禅者的心具有三个特点,我曾经把它概括成“禅心三无”。哪三无呢?
第一是无忧。禅者从来不会为未来担忧,不会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得失利害而担忧,也不会为自己死后怎样而焦虑。他是彻底的无忧。不是生活里有吃、有穿、有住以后的无忧无虑,而是对于生死大事的无忧。
第二是无悔。禅者从来不会为自己过去的言行而后悔,不会因为自己过去的事做错了,心里就背包袱。已经过去的事,在他的心中没有任何积压。这不是说他忘记了,而是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他的心就像竹篮打水,永远是空的。我们普通人则不然。我们的心往往装了很多东西,过去的东西全都装在里面,越装越多,活得很累。我们过去做了错事,很后悔,可是又不能从头开始,所以徒然后悔,给自己造成了很大压力。很多人说,如果再过一次就好了,一切从头开始。可这是不可能的,过去只有一次,不能重新再来。
第三是无怨,没有抱怨。禅者对于现在的处境,总是正面地接受,不逃避。他是以正面态度对待落到身上的一切,无怨,总是欣赏,总是感恩。
可见,立处皆真就是安住当下,不纠缠过去,不希冀未来,也不在现在的抱怨中。心在哪里呢?心永远是现在进行时。在生命的每一个当下正在发生的,我们要全力以赴、全体承担,安住在当下。跟过去,斩断;跟未来,斩断;跟现在的牵连,斩断。
从这里解脱,就叫安住。
第三,做牛做马。做牛做马是指奉献。禅者从自私里解脱出来,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奉献。大慧宗杲禅师有一首诗:“桶底脱时大地阔,命根断处碧潭清。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前面两句是讲开悟的过程,“桶底脱时大地阔”,比喻心窗打开,光明透亮。“命根断处”是指意识之流断了,过去一向以来对待事物的方法、态度全然被转过来了。开悟不是得到某一个观点,而是对待世界人生、包括对待自己的整个态度,全都转过来了,来了一个大翻身。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呢?“好将一点红炉雪”,我们的烦恼好比是雪,它在智慧的红炉里马上就会化掉,转变成为奉献,“散作人间照夜灯”,认识了烦恼即菩提以后,再回到人间去照亮黑暗、照亮他人。
中峰明本禅师讲,开悟以后的祖师,有各种各样的行为举止、各种各样的生活道路,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他的道理和用心。有的到深山老林里隐居;有的到人间,像道衍禅师,参与世间的事;也有还俗的:元朝有位宰相叫刘秉忠,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位禅师,后来他做了忽必烈的近侍,最后做了宰相。蒙古人刚刚到内地来的时候,对中原文化不了解,做了很多蠢事,比如说,把种粮食的田地改成种草、作牧场等等。当时就有很多高人给元朝皇帝提建议,要他择用汉地的读书人为官,管理地方行政,种粮的地不能种草。这些意见就是由刘秉忠转呈给皇帝的。刘秉忠对于保护中原文化、引导蒙古人适应内地文化,起的作用特别大。他以前就是个出家人。
有一位禅师开悟以后,到河边摆渡,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要是现在,那就不得了,如果我说我是大禅师,马上身价百倍。那个时候他去摆渡,如果是现在,也许会去做出租车司机,少收钱,或者不要钱,做好人好事。还有的禅师开悟以后,在十字路口搭个茅棚,每天在那里煮水,给大家施茶。因为过去交通不发达,人们用脚力赶路,往往会感到很渴。还有的禅师开悟以后,专门修路。虚云老和尚就碰到过这么一位修行人。有一条路特别长,路况很糟糕,但是没有人修。这位禅师一个人去修,今天搬一块石头,明天弄一筐土,最后把这条路给修起来了。
禅者悟后的生活,虽说是回到了人间,但是心态跟悟前大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他完全是随众生的需要,做帮助众生的工作,没有什么佛不佛的观念,更没有自我意识。众生要吃饭,如果我跟他讲佛法,他能饱吗?他要吃饭,我们就只能给他饭吃。如果他有病,跟他讲佛经,病能好吗?就得给他医药。众生贫苦的时候需要致富,如果我们在那里打坐,能把钱弄来吗?不行。所有众生的正当需求,我们都要帮助他们,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再引导他们向道。等他吃饱了、病好了,突然想起来,哎哟,我心里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生死大事没有解决,我生前从哪儿来?死后到哪儿去?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讲,过来过来,我给你讲信仰、讲佛法,教你打坐。但是在这之前,需要做很多利益众生、随顺众生的工作。
古代禅师常常用《十牛图》来描述修行的历程,最后一幅图叫“入廛垂手”,廛就是街市上的铺面。开悟的人,最后到街上去,到店铺里,到酒吧、甚至妓院里去,到卡拉 OK厅,也去唱歌、跳舞,通过这些方便,让很多人改邪归正。垂手是把手伸出来拉人的意思,走到街上的店铺里去拉人。修行到最后,就是走入人间。这种境界只有开悟的人才做得到。如果没有开悟,就不要去;你自己如果没有得到自主、自在,就跑到卡拉 OK里去唱去跳,唱着唱着,自己就会迷到里面去了,没有帮助人,反而被别人拉进去了。要跳到水里救人,必须自己先学会游泳。
沩山禅师去世以前,庙里的首座和尚问他,你死后要到哪里去?沩山禅师说,我要到山下的施主家做一头水牯牛。不一定他真的就去做一头牛,他的意思是指,他要去为众生当牛作马,众生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个时候,他的心完全自在了,完全被调伏了,所以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真正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禅者的精神风貌、人生态度和心地境界,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他的悟处高远,解脱独立,孤峰独宿;他的生活态度,是安住当下、立处皆真;他的价值取向,是无我奉献、当牛作马。
参禅的方法——无门关
下面讲禅宗的参禅方法——无门关,它渊源于我现在所住的赵县柏林禅寺。唐朝末年,有一位大禅师在我们寺院住,通常人们称他赵州禅师。赵州禅师法号从谂,山东人,很小就出家,很年轻的时候就开悟了。他 80岁以前,到处参访善知识,寻师访道, 80岁以后才在柏林寺住, 120岁去世。他的禅法对中国禅宗,乃至对传到日本、韩国、欧美的禅,都有深远的影响。无门关这种参禅方法,到现在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欧美、日本、韩国,学禅的人都从无门关入手。
无门关来自于一个公案。有一位修行人问赵州禅师:狗子有没有佛性?佛经里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个人当然是明知故问。修禅的人问问题,都不是随便问的。赵州禅师的回答是:无!这个回答与佛教的常识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赵州禅师说的“无”,并不是有无的无,他的心已经超越了对待——有无、是非、来去、一多、美丑、生死,超越所有的对立之后,就是绝对的禅心,就是佛性。所以赵州禅师说的这个“无”字,等于是把他自己的心掏出来了,和盘托出。
后来的禅者,就在赵州禅师的“无”字上用功。他们想: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赵州禅师为什么说“无”呢?为什么?当我们把所有的妄念、所有佛经里关于佛性的理论知识全部抛开,将所有的力量专注在这个“无”字上的时候,人的心就会死掉。大死一番,然后才能大活。最早提倡无门关的,是宋朝的大慧宗杲禅师,之后又有一位无门慧开禅师,他写了一本书就叫《无门关》。这本书的第一则语录就是讲的这个公案,并由此形成参无门关的修行方法。
大家看——赵州和尚因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然后,无门慧开禅师就发表他对这个公案的看法说:“参禅须透祖师关,妙悟要穷心路绝。”这个透,不是在大脑中理解,而是要在心里透过祖师关。什么是祖师关?就是祖师在种种公案语录里面,和盘托出的禅心,在一问一答之间吐露的心地光明。我们能透过祖师关,就意味着我们和禅师的心地光明接上了。祖师的言语问答,往往和佛经里的说法不一样。什么是佛啊?砖头。什么是达摩祖师的禅法?庭前柏树。这样回答还算是比较平实的,还有其他更奇特的回答。你问他什么是佛?吼你一声,或者当头一棒,就是他的回答。参禅,必须要能够从祖师的问答言语中透过去才行。
“妙悟要穷心路绝”,真正的妙悟,必须要把意识之流,把我们有生以来、乃至生生世世走惯了的心路,在这里断掉,就像飞机起飞一样。我们骑自行车永远飞不起来,坐在火车上飞不起来。我们要飞起来,必须要放弃这些方法。我们用心路去推测、判断、思维、归纳、总结,我们不可能真的增加什么。现在人类的知识大爆炸,并没有给人的心灵上增加什么。相反,在心路绝的地方,我们才会有新的发现。
无门慧开还说:“祖关不透,心路不绝,尽是依草附木精灵。”所谓依草附木的意思是说,你的心不是独立的,你总是依赖于种种的意识形态、观念、概念、思维、结论。“且道如何是祖师关?”祖师关是什么呢?无门禅师说,赵州禅师回答的“无”字,就是我们要过的祖师关,它是一个“无门关”。如果你的心能够透过这个无门关,就可以和赵州禅师的心接上。赵州禅师超越了有无、是非、来去、时空、一多、你我、美丑所有的二边对立,如果你也能开发出这个绝待之心,那你就亲见赵州,也就亲自见到了佛。佛在哪里?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佛的形象来找佛,要见佛,就要见佛的心。亲见佛心,就与佛平等——“便可与历代祖师把手共行,眉毛厮结”,透过了无门关,历代祖师都跟你是朋友,是一家人、亲兄弟,所闻所见都是一个样;眉毛厮结,头与头碰在一起。“同一眼见,同一耳闻,岂不庆快!”
怎样才能透过无门关呢?参“无”的方法,是要“将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毫窍,通身起个疑团,参个无字,昼夜提撕 ”,以整个的身心全力以赴,一天到晚在心里参这个“无”。佛经上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赵州和尚为什么说无呢?“莫作虚无会”,你不要把“无”当成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无”,错啦;“莫作有无会”,不要落在两边。“如吞了个热铁丸相似”,他打比喻,在参“无”的时候,有个热铁丸吞到肚子里面,吐又吐不出来,进不得,退不得,山穷水尽,绞尽脑汁,所有的路都试过了,都不灵验,找不到答案,非常苦闷。在这个时候,我们后天熏习的各种见解、恶知恶觉,就会被这一个“无”打发掉,歇下来。
“久久纯熟,自然内外打成一片,如哑子得梦,只许自知。”哑巴做了一个梦,说不出来。“蓦然打发”,忽然有个外缘,像香严智闲禅师,有瓦片打到竹子上面,发出清脆的声音,通过这样的外缘,疑团破了。“惊天动地,如夺得关将军大刀入手,逢佛杀佛,逢祖杀祖。”这个杀不是杀生的杀,这个杀是说,噢,明白了佛祖的心,明白了佛祖讲的话,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障碍自己,不再执著了。“于生死岸头,得大自在;向六道四生中,游戏三昧。”佛教讲生命有很多层次,有解脱自在的圣人,也有在六道中轮回的凡夫。开悟的人,他同样生活在凡夫的境界里面。那么他在这里做什么呢?玩。这个玩不是我们理解的贪玩的玩,而是说,他在做种种事业帮助众生的时候,不会觉得累,不会觉得有什么,做了很多,好像没做,闹着玩,所以叫游戏三昧。好的时候玩,坏的时候也玩,活着的时候玩,死的时候同样是玩。
禅师在死的时候玩,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死的时候怎么玩呢?临济禅师住河北正定的时候,寺院里有一位普化禅师,这个人成天疯疯癫癫的,在街上来来往往,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一天他突然跟别人讲:哎!给我做一条大褂。有人就做了大褂送给他。他说不对,不是这个大褂。临济禅师是一个得道高僧,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跟寺院管事的说:那个普化要死了,给他做口棺材。棺材做好了,普化就扛着棺材天天在街上跑,说现在我要死了,快来看,看我怎么死。他先跑到正定县城的东门,大家听说高僧要坐化了,都过来围观。他说哎呀,今天时间不对,明天再说。第二天他跑到南门,又找了一个借口,说明天再说吧。第三天跑到西门,还是有很多人跟着,他又找借口说不行。最后大家说这肯定是开玩笑了,他是在骗我们。到了第四天,他到北门就没有人跟着了,因为他这个“狼来了”说了好几遍,人家知道他撒谎。到第四天没有人跟着的时候,他自己跳到棺材里,拿着钉子锤子,然后交给过路的人,让过路的人把棺材钉上。过路的人也奇怪,竟然按他的吩咐,把棺材钉上了。钉上以后,赶紧回到临济寺报告:方丈啊,你们这儿的普化禅师在棺材里坐化了。大家呼啦一下子全过来了,最后把棺材撬开,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听到天空中隐隐约约有吹箫的声音渐渐远去。这就是玩死。
有一位禅师叫邓隐峰,去世前问身边的弟子:过去的高僧都怎么死呢?弟子回答说:有的坐着死,有的躺着死,还有的站着死。他说你们有没有见到过倒立着死的?没有。他说看我的,倒立而化。倒立去世以后衣服还是顺着身体贴着,不垂下来。别人推他也推不动。后来他的妹妹,也是出家人,过来说:哎呀老兄,你活着的时候很调皮,死的时候也要跟我们开玩笑。推了一下,倒下了。现在五台山北台还有个白塔,那就是邓隐峰的舍利塔,这个故事就是在那里发生的。这叫游戏三昧。当然不仅仅说死的时候玩,活着的时候也玩,帮助众生,做很多利益众生的事。
下面说:“且作么生提撕?”提撕,就是在心里不断地举起这个“无”字。“尽平生气力,举个无字,毫不间断。好似法烛,一点便着。”在生活中,我们在“无”上起疑情,念念不间断,行住坐卧,白天黑夜,全力以赴——打一个比喻,一个万丈悬崖,你吊在一棵树上,你敢松手吗?松手就摔死。所以把生命所有的一切,都专注在“无”上,吊在“无”这个字上,其他的全放下,只有这个地方不放下,那么就有机会。这个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当然,在那种心态下也不会动念去求,自然一定会有一个外在的因缘,听到一个声音,看到一个什么——噢!明白啦!明白了赵州,看到了他的心;明白了“无”,也明白了所有的佛祖。就是这么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可以盘腿静坐参,可以走路参,也可以躺着参,都可以。它在宋朝以后非常流行,很多修禅的人就是参“无”字开悟的。这个“无”不是没有。这个“无”我们用语言、思量没办法透过。怎么办呢?只有用心直接去透、去跟它搏斗。
大慧宗杲禅师关于怎么参“无”,有很多开示。他说:在参“无”的时候,“不得作有无会,不得作道理会”,不能在心里去找一个道理,这些我们都太习惯了,一向以来都在这里面,我们还是我们,没有变化。现在我们要脱胎换骨,要换一个人,换一个心,所以平时习惯的有无、道理,都不要。“不得向意根下思量卜度”,意根就是意识,不要去寻找某种特殊的感觉。“不得向扬眉瞬目处挆根”,扬眉,扬起眉毛;瞬目,转动眼珠。有的祖师在接引学人的时候,有时候会举一个手指,或者竖起拂子,来表示禅的境界。你也不要在这些行为动作中找答案。“不得向语路上作活计,不得在无事甲里……”你也不能坐在那里空空无无,什么都没有。“但向十二时中、四威仪内”,在一天十二个时辰、行住坐卧四威仪当中,“时时提撕,时时举觉: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不离日用。试如此做工[功]夫看。”这样做功夫看看。这是大慧禅师给他的一位在家弟子的信里开示的,适合在家人修。“月十日,便自见得也。”一个月的工夫,你就会有体会。
这个方法,实际上是要借这个“无”字,截断我们的妄想之流。你平时习惯的路已经被堵塞掉了,没路可走了;所以要把平时习惯的思考、引证、观点、见解、积累的知识全部放下。这一点现代的人特别难以理解。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德国的天主教神父,他现在也学禅,他教人家参禅,就教人们参“无”。他在柏林寺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我说你们在欧洲传禅有什么体会?他说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很难接受。对于所习惯的思维、念头之外还有什么,他很难理解。那样人不就死了吗?不就无路可走了吗?我前面所讲的大死一番,就是指的这个。在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东西透过“无”呢?用心。没有任何别的工具了。祖师讲,平时所知道的道理、佛经上的话、老师教的诀窍,全部放下,直接用心去碰、去接触。所以那是一场肉搏战,可能你会觉得很苦闷,很枯燥,找不到路。欸!正好,这才是对的,一定要坚持。就在这个时候坚持一步,就会有突破。即使没有突破,心地上也会有开发、有进展。
在这里我想说明一点,我们现在学禅,不要念念把开悟当一回事,这样的念头会成为开悟的障碍。只要你去做,就会有收获,开悟不开悟,让它自己去。只要你做,就会有进步,你的心地会越来越亮。我个人觉得,无门关的方法,是我们入禅的方便之门,是我们进入禅的堂奥的入手处。我也觉得,无门关不仅仅是入禅的方便之门,也是一切正常健康的人类宗教获得神秘体验的入门处,是真正获得宗教体验的下手处。为什么?一切真正的宗教体验,都是超越对待的。只有在我们平时的心路歇下来的地方,真正的宗教体验才会产生。
丹麦有一位基督教哲学家,叫克尔恺郭尔。他有一本书叫《恐惧与颤栗》,其中讲到《圣经》的一段,上帝对摩西说,把你的儿子带到山上,杀掉他。我不是研究基督教的,但我觉得这些话是有宗教寓意的。《圣经》里说,摩西第二天起来,带着儿子到了山上,准备杀掉。当然在那里他见到了上帝。我们听起来真是骇人听闻、不能接受。把儿子杀掉,这完全是灭绝人性的。克尔恺郭尔是绝对讲信的,分析的时候他说,在那时候摩西心里什么都没想。我觉得虽然是基督教,但是它在这个地方,也是透出了平时的心路,进入到体验里面。实际上他也不会杀,最后他也没有杀,只是虚惊一场。它所包含的宗教寓意,是在我们平时所执著的心路,那些对立分别、那些我们抓住不放的地方,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往前跳一步。用禅宗的话来讲,就是“悬崖撒手”,在悬崖边上往前跨一步。我们说往前我会摔死啊!跳过去,死不了。跳过去就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超越有无、是非、美丑,超越一切意识形态,让我们的心从意识形态、思想情绪、知识见解里解脱出来,这是我们进入真正的宗教体验的入门之处。如果不经过这里,我们得到的永远都只是知识——关于宗教的知识,关于修行的知识,心里没有体验。这是我向大家介绍的禅法“无门关”。你们如果有机会到柏林寺去,可以在我们的禅堂里体会体会。
提问:怎么去体会?
明海法师:就是要用这个“无”,把我们心里的各种见解、各种知识、各种情绪剿灭掉,最后从自心、从内在,自己明白。
问:明白什么呢?
答:明白你自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明白的人,心是空的,本来无一物。但是你不要点头,你一点头就错了,一点头等于你接受了这个结论,就把你障碍了。
问:自己明白之后能不能讲给别人听,让别人也明白?
答:可以。但是你无法代替他,他得自己去做。
问:明白就是知道?
答:知道不等于明白。知道有时是在知性上知道一个结论。我建议大家每年或者每个礼拜啊,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把工作放下,集中时间来打坐,在心灵上做一个开发。可以在寺院,也可以在自己单独安排的地方,比较封闭的地方。这对工作也是有帮助的。据我所知,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经常这样做。多年来护持我们寺院的香港旭日集团的几个老板,他们都会专门安排时间用来打坐、用来闭关。完全放下,专门在心地上静下来、沉淀下来,再出来制定发展战略。这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我们每年有一段时间,用无门关的方法用功,相信会有发现和突破。
版权所有:药师经问答网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