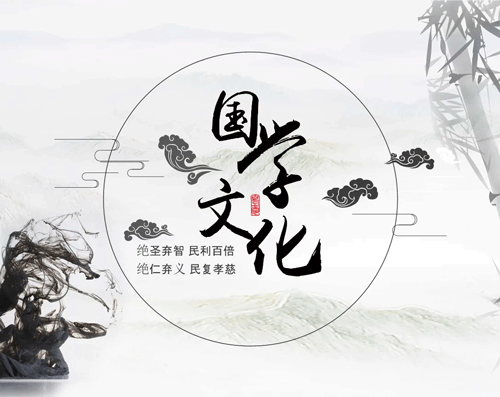什么是佛法
发布时间:2023-08-28 12:57:00作者:药师网眼前有些善男信女,还抱着一腔“忧惶”、“悲痛”的心情,认为佛法在走厄运,法有被消灭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研究过佛法,也敢轻率地肯定佛法为迷信、为落后思想,武断佛法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必须会为时代所遗弃。很显然,后者这种形式主义的错误看法,完完全全是从前者善男信女的一些错误言论与行为所激发起来的。这是沉压在佛法上面的一个旧包袱。因此,我想霸蛮运用自己的一点气力,来说明一下佛法的本质,以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与看法。读者如在下面发现有歪曲佛法的地方,我诚恳地请求读者毫不吝惜向我多提意见。
我有一位熟识的老修行,他早就感伤丛林里没有了佛法的气息,独自跑到市区附近一个破庙里过着他的锄头主义生活。因他为人诚朴、和蔼、又从事劳动生产,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左右邻居都认为他是一个本色出家人,对他都相当好。解放后,他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身体也越来越硬朗。
有一天,我落宿在他破庙里。他照顾我吃了饭又照例递给我一碗茶后,他靠近我坐下。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探身向前低低地问我:“你看,佛法是不是还能存活下去?”
我愕然望了他一眼,逗得我反问他说:“你讲,什么是佛法?”
他嗫嚅地说着:“这,这……”几乎说不出话了。
我说:“我与你的看法绝然不同。我认为我们这些自认为释迦弟子的已经是‘无\’佛法了,因而更谈不到能不能存活的问题。”
他说:“我也同意你这种看法。你想,有许多人说他不是佛教徒,他又住在庙内,或加入了佛教团体,或者在家里看经念佛;说他是佛教徒吧,从他的脑顶一直嗅到脚板心,又实在嗅不出一点佛教徒的气息。”
我说:“我的意思,不是你这样说的。”
他说:“照你,又怎么讲?”
我说:“我问你,四摄、六度是不是佛法?”
他说:“佛说的,怎能说不是佛法啦。”
我说:“你想想看,四摄六度中,那一摄、那一度不能在新时代里存活下去?”
他笑盈盈地说:“如劈旃檀,片片皆香;你又能叫我说那一片旃檀不香哩。”
我说:“惨痛或惭愧就在我们这些自称是释迦弟子的人的身上,这种旃檀的香气太少了。”
他喟然地叹了一口气,说:“惟其如此,所以佛法就不能存活下去了。”
我说:“菩萨,你又搞错了。现在是香气过于微渺,或者说根本没有香气,而不是香气散放不出去呀。”
他点点头,说:“是的。”
我说:“你的病根,仔细分析一下,就是将寺庙,僧尼这些形式认成了实相般若——识成了佛法,忘记了这些形式只是表现佛法的工具。而且好像还忘记了眼前这些工具,百分之九十以上几乎都不能表现佛法了。因为你的思想对于这个道理混淆不清,所以就形成了这种错误。你还来苦恼地问我“佛法是不是还能存活下去?”
他犹豫了一下点点头说:“你说得是。”
此后,我们兀坐相向,默然不语。我实在有点儿耐不住这种沉寂,只好又故意地向他挑逗说:“你说四摄、六度法中,为什么皆以布施排居第一位?”
他兴奋地回答:“假如我们不能如实地修习布施,则其余的三摄五度必将流入邪行;一切佛法,也将变成了不能饶益众生的空话。”
我对他这种“一针见血”的透辟说法,也只有心诚地向他连连点头。
他又补充着说:“离开了泥土水分,枝叶繁茂的果树是生不出来的。众生,就是菩萨成就无上清净功德的泥土水分。菩萨如不欣跃地依止众生,菩萨是将无行可修、无道可成的。”
我说:“我们平常不是唱着‘布施度悭贪\’吗?”
他说:“是呀。”
我说:“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布施,是佛法;悭贪,非佛法。”
他寻思一下,说:“根据一般的观点,是可以作如是说的。”
我说:“悭,就是吝惜自己的财物而冷酷无情,遇见众生陷入饥饿、厄难、痛苦、死亡的时候,还能漠然无动于衷,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肯做。”
他微笑着说:“你讲得很通俗、很具体。”
我说:“贪,就是为了增积自己的财富,还要更进一步地利用欺骗、权势或其他不法的行为去剥削别人,残酷地吸吮别人的膏血以肥腻自己的身家。”
他丧气地回了我一个“嗯”,并用丧气的面孔望着我。
此后,我们又兀坐相向,默然无语。也许他也有点耐不住这种寂寞吧,忽而一道喜悦的光辉从他的眼角掠出,睛光一闪,他又敛容向我说:“古来有‘叶公好龙\’这样一则公案,说叶公好龙,门窗楹壁、几案盘盂之上,几乎都画满了各色各样的的龙形,起坐食息,无不注赏以为乐。天上的龙听到了,窃然自喜,以为叶公真是自己的一个知己。等到这一条真龙从空宛转飞跃而下的时候,叶公却几乎骇昏了、骇死了。我想我自己同许多崇信佛法的四众弟子,的确有点‘叶公好龙\’的风味。”
我因他引喻微妙,亦不自觉嗤嗤而笑。
他说:“佛法讲布施,不是有财施、法施、无畏施三个系列吗?”
我说:“是呀。”
他说:“布施的对象,就是众生。离开了众生。菩萨的布施功德是扎不稳根的。”
我说:“是呀。离开了我这一位众生,你现前的法施功德就扎不稳根了。”
他也故意地呵斥着说:“不要调皮。你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吧,菩萨布施功德,为什么要在众生身上才能扎得稳根呢?”我说:“因为众生不是顽冥不灵的木偶。”
他说:“这话怎么讲?”
我说:“因为众生有‘离苦得乐\’的欲求。”
他说:“是呀,我们必需将自己的生命与众生的生命相融化。关心众生的生活,了解众生的境况,深刻地体验众生苦乐心情,帮助众生去解除束缚、压迫的痛苦,满足众生快乐的愿望,我们才能完成布施功德,我们的布施才能扎得稳根。”
我说:“在过去旧社会里,我对于你这种说法,是能够完全同意的,但是在眼前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时代,现实生活给了我最珍贵的教训,我觉得内容还有加以部分修改和补充的必要。”
他迷惘地望着我说:“你讲吧。”
我说:“佛法是强调‘平等\’的,如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清净平等’、\‘平等佛性’这一类的词句,是充满在大乘经论里面的。这意思就是说佛、如来,并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特殊阶级,任何众生皆能加强自己的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任何众生皆能彻底发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就是说任何众生皆具有觉悟的可能性,皆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并不比众生多一点什么,众生也并不比佛减少一点什么。不过是一个见得到,做得到,一个还未见到、未做到,或者说自甘堕落不愿见、不肯做而已。这还是侧重学习、文化方面平等讲的。在物质生活方面,印度原始的佛教制度我们不说了。中国当唐朝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的时候,就极力主张共同劳作、共同享受。百丈衰老了,大家尊敬他、爱护他,私自将他的农具隐匿起来,不忍他一道儿同大家在田间劳作,恐怕累坏了他年老的身体。但是他却以‘绝食\’抗拒大家的意见,坚持参加集体的生产,故有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美谈。世尊住世时,争着为他年老眼花的弟子穿针。有许多僧尼在百里之外化到斋粮了,即使途中饥疲不堪,他认为斋粮是以大众的名义化缘来的,在庙内大众还没有受食的时候,自己先在路上私自吃了,这是违反戒律的,对大众不起的。因此他宁肯忍受饥疲,而不愿私自侵损大家的权益。他们这种行为,虽似乎有点过于迂拘,但他们的这种精神确是值得我们歌赞的。流风遗韶、顽廉懦立。自在过去旧社会的丛林里,即使是一个惯于侵损剥削大众师傅的贪污份子,在真理的威严底下,也不能不被迫地俯首承认‘利和同均\’、‘粒米同餐\’的佛法生活是优越的、是正常的,而只有暗自让矛盾的痛苦扭绞着自己的神经。这深刻地说明了佛法的实质是反阶级压迫、反阶级剥削的。”
他说:“你现在所引用的‘利和同均\’、‘粒米同餐\’,与俗话说的八两,半斤,二五一十,字形、字音虽不同,而所表述的事实却是一致的。我们有些佛教徒,几乎知八两而不知半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于是本自博大精深、圆融无碍的佛法,被这些佛教徒弄混淆了。”
这样,由于他过分对我的刺激,使我又加深了一分感触。因而我对他说:“菩萨!恐怕我们有些释迦弟子连‘八两\’、‘二五\’都不能如实地真正知道呢。你想:八两半斤、二五一十,在实际上所诠表的还不是一个同样的数目么,如能在实际上真知‘八两\’、真知‘二五\’,断不会在实际上不知‘半斤\’、不知‘一十\’的。举例说,我们成天按时敲得木鱼震天响,高唱‘众生无边誓愿度,法门无量誓愿学’的偈语,甚且强调‘自性\’一词,兴奋地唱着‘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法门誓愿学’。关于\‘自性’一词,我真不懂,我们自己是如何体会的?如言离了现实世界里面的众生,额外还有‘自性\’,额外还有‘自性众生\’。把佛法、世法生硬地打成了两橛,这是近乎外道的邪解。但是我们却不能关心现实众生界的生活,不能与众生气自相贯、血脉相通,不能把大伙儿的甜酸苦辣,喜怒悲欢融成一片;我们只成天按时关着山门高唱偈语,这能说是真知‘八两\’、真知‘二五\’吗?正是你前面所说,我们所好的是画龙,一旦真龙破空飞来的时候,我们反而骇得要死了。”
我静静地盯了他一眼,随又说:“严正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日常生活资料粒米缕丝寸椽片铁,莫不浸透了劳动人民的辛苦血汗;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却终年累月过着牛马奴役的艰苦生活,有时还要在饥寒疾疫的地狱里面挣扎。许多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却反而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种田的无饭吃,不种田的肉汤淘饭,却反而皱着眉头嫌油腻了没有味道。这是不是释迦弟子所向往的平等世界?释迦弟子对于这样现实的腐朽血腥罪恶世界,是不是应该有个善恶是非的分辨?劳动人民为了解除自己压迫剥削的惨苦,重新创造一个光明美妙平等自由的幸福世界。不能不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猛烈顽强地斗争,而我们有些释迦弟子在这翻天覆地的斗争里面惊惶失措、莫知所向,询不知我们平日研究何物以为佛法?要将我们自己信受奉行的佛法摆在什么地方。”
他说:“佛法能不能存活下去?经过了你刚才反覆的解释,自觉虽然豁通了一点。我很希望你能进一步的在这上面多多发表一点意见。”

我说:“你前面讲布施时,我说有加以部分修改与补充的必要的地方,也就顾虑到了这一点。我们无妨先将什么是佛法,世法撇开,准情酌理、称性而谈好了。”
他说:“行,听你采取什么方式讲。”
我说:“假定有一只恶狗向你猛烈扑咬时,你是同它讲慈悲?还是同它作斗争?”
他稍加沉思说:“在我,还是一个‘身见\’未破、怕痛怕死的凡夫,当然只有同狗作斗争。”
我说:“记住,你自己因为怕痛怕死,被迫的是不能不向狗作斗争的。”
他眯眯地瞅着我笑。
我说:“假定你是一个身见已破,不怕痛也不怕死的菩萨;但是你恰好也遇到了一个身见未破,怕痛怕死的凡夫,正当被恶狗猛烈扑咬时,你是劝这个凡夫同狗讲慈悲,还是帮助这个凡夫向狗作斗争呢?”
他眼光在我脸上打了一个盘旋,还是眯眯地瞅着我笑。
我说:“痴痴地笑什么?恐怕你心里还想感化狗,要狗回心向善不再无理扑咬了?”
他眼光又在我脸上打一个盘旋,还是眯眯地瞅着我笑。
我说:“你这样眯眯地笑,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是不诚实、不坦白。拉倒!我们还是养息去吧。”
他说:“你着什么死急,我要你替我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当然会讲呀。”
我说:“讲!讲!”
他说:“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家、恶霸地主,大半都是一些顽冥不灵的恶狗。只有粗棍才能降伏他,才能叫他慢慢地回心向善;磕头,说好话,要他讲慈悲,不侵害人,不向人扑咬是做不到的。广大的劳苦人民,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为了逃避自己的痛苦与灭亡,当然只有进行严肃地斗争。假如逃避自己的痛苦与灭亡,当然只有向狗进行严重地打击。假如我们劝广大的劳动人民放下自己的武器,永远驯服的让少数剥削阶级者骑压在自己的头上,咬紧牙齿忍受痛苦地灭亡,佛法的慈悲即将变成愚凝与残忍的罪恶,我们自己也就不自觉地变成邪魔鬼怪的帮凶。世尊与佛法,是会为我们这些愚昧的弟子所扼死的。假若恶狗无故欺负人、侵害人,向人猛烈扑咬的时候,我们对于被扑咬者熟视无睹,还要站在超阶级、超政治的立场,不能帮助被扑咬者向狗进行严重的打击,佛法的慈悲即将陷于善恶不分、是非不明的麻痹状态亦失去‘饶益有情,严净国土’的伟大效用,这恐怕也有点乖忤世尊大慈大悲、说法度生的本怀吧!”
由于老修行的词锋精锐、刀刀见血、激起了我异常的惊喜。因而我拍着他的肩膀誉勉说;“菩萨,你真是可以说是‘一拨便转\’了。这就是我们必需倒向一边必需加强向劳动人民学习,改造自己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理由,也就是不能容许我们站在狭隘的模糊的宗教立场,以遗羞佛法自失善利的理由。”
他说:“我平常还有这一点模糊的认识——只要有阶级社会存在,就决不能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血腥的统治阶级,极惯于利用这些狭隘的观念麻醉人民、驱遣人民,以作为他们进行侵略战争的工具。因为有阶级社会存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里面的统治阶级,绝对不能获得利益的调和,由于彼此争夺殖民地与行销货物的市场,各个帝国主义者在利害观点上就存在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尖锐矛盾。帝国主义者与剥削的弱小民族,由于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对立,又存在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尖锐矛盾。假若我们大家不努力改造自己面前的世界,则人类对于威胁毁损残杀自己的血火战争,就会永远重复表演,绝无根除希望。一个佛弟子是愿望人类互相屠杀下去,还是愿望人类比较真实性的长久和平局面涌现出来呢?假如他真是关心生活的佛弟子,我相信他是会替自己拣一条光明大道的。”
我说:“你这种看法,完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一点儿都不模糊,我们也的确应该自己拣取一条光明大道了。”
他说:“我们还得将话头拉转去。佛法向来讲平等的,不分相的,无冤无亲的。而我们现实生活中则必需强调划清敌我,爱憎分明,一点儿也不容许含糊。难道二者在这一点也不能融会贯通毫无隔碍吗?”
我说:“佛法里讲魔讲怨而且要彻底发挥大无畏的精神降伏魔怨,有时候甚至赞叹慎愤杀戮为清净行。菩萨低眉是佛法,金刚怒目也是佛法,所以佛法里面所讲的慈悲,决不是软弱、决不是惧怯,更不是感情麻痹。不错,佛法是讲 ‘平等一如、无冤无亲\’的,但这两句话最好的解释也就是说在佛法里最正确的解释,就是世尊的生命,是与无量众生的生命相融化的,此中本自‘平等一如无人无我\’,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冤\’与‘亲\’哩。这的确是佛法最基本的立场,每一个佛弟子都应该信受奉行,不容歪曲,也不容逾越的。这毕竟只是个‘理\’、是个‘真谛\’,我们平常说‘真俗无碍\’、‘事理圆融\’,又说‘散一理而万殊摄万殊而归一理。\’足证这个理,这个真谛不是在我们日常尘劳事用以外的。所以禅宗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说‘平常心是道\’,说‘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教中说\‘依理起行’也就是要我们在日常理务中起心动念、待人接物,都应该坚持这真理来做自己的生活的准绳。又说‘依事显理\’,不是更明白的告诉我们,只有依据日常生活事务,才能表现这种佛法,才能表现这种真理么?我们必坏世法而别求佛法,必拨弃日常事务而契证什么不可思议的真理,敢保必将陷落黑山鬼窟,将自己浸杀在不藏龙的死水里面。我们必需领悟这点道理,才能进一步了解‘无冤无亲\’和无‘降伏魔怨\’本自可以无障无碍、并行不悖的。为什么?因为世尊‘等视众生,犹如自己的一身’。我们对于自己的一身还会有什么隔阂吗?还会有什么虚妄的亲疏分别吗?但是在这本自平等一如、无冤无亲的身上,不幸生了一个毒疽,对于整个身体有着极其严重的影响,甚至性命的危险,我们是不是需要将它怒痛地割去呢?当然需要的,十分需要的。我们只好咬紧牙齿,忍着一阵剧烈的痛苦将自己身上的这个毒疽割去。不然,在大慈大悲平等一如的世尊心目中,为什么还有魔有怨?而且激动菩萨,彻底发挥大雄无畏的精神降伏这些魔怨呢?这恐怕决不是那些佛法看成‘超阶级\’、‘超政治\’的同参道友所想得通吗?不错,我们现实中主张与剥削阶级斗争,并不一定是要消灭肉体,而是要彻底改造剥削阶级的思想、消灭剥削阶级的制度。这正如你前面所说的‘恶狗怕粗棍\’,没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是不能镇压、降伏这些恶魔的,是不能强制改造这些恶魔的思想,使之回心转意,自觉自愿来向人民低头、来为人民服务的。假若容许我们以佛法的术语,也就是‘大慈大悲\’与‘大雄大力\’相结合,所以只要我们能突破狭隘的宗教观点,体会佛法真实的精神,在这划时代的社会里,纵目所观,几乎随时随地皆可能得到活生生的佛法。假若我们这些自承为释迦弟子的人,不能翻然觉悟蓦地回头,我们自己的法身慧命,也必将会坐在这新时代的饭笼里白白饿死。”
老修行嘘出了一口沉重的气息,好像卸下百二十斤的担子一样,轻松愉快对我说:“谢谢你,我已经知道了什么是‘佛法\’了。”
(原载《现代佛学》一九五二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