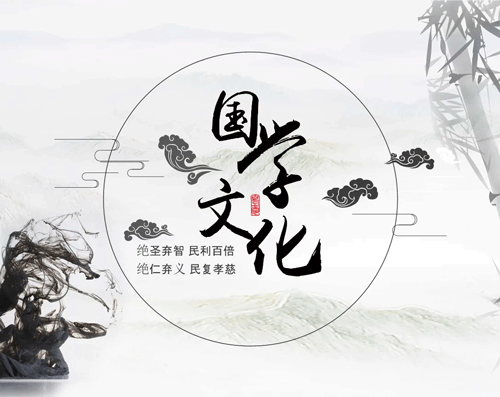想到了剃度师
发布时间:2023-11-14 13:00:25作者:药师网
今天看来,家师是一位思想比较保守的老和尚。他的出家,更多是受到家庭的影响。据老人自己介绍,家中祖辈就有人信佛。尊重父母的安排,他曾娶了位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
学佛之后,他经常去离家不远的居士林参加活动。后来,抗战开始,人员日渐稀少。他索性就住到了那里,一边读经念佛,一边帮助看守房子。
日本人打到宿县时,在当地抓了不少人。一天,老人在外出回去的路上被日本兵撞上,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带到了宪兵队。大家被命令站在一面围墙下,不远出,有一只凶恶的狼狗虎视眈眈的望着他们。天气很热,太阳下的温度不低。日本翻译要他们交代游击队的情况,否则就拉下去喂狗,胆小的早已吓的说不出话来。老人不慌不忙,口中一边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边劝其他的人,放下一切想法,专心忆念菩萨。过了大约1个钟头,宿县保长进城交粮恰巧路过此地,发现被关住的老人和其他几个熟人。由他出面证明,几个人获得自由。
自此之后,老人坚信与观音菩萨因缘笃深。功课之余,常以宣纸绘出各种不同类型的观音造像。如:竹林观音、水月观音、南海观音、提蓝观音等等,赠送有缘之人。
老人自小师从乡里的几位画匠学画,或许有宿世的习气,进步颇快,20岁左右就在县里小有名气,并以山水与动物著称。在回忆年轻时候,他提到曾经画过一只老虎,虎须栩栩如生的样子。问他现在为何不画动物,他说画什么心里就会想什么,还是画佛像最好,念佛成佛。
老人属于半路出家。解放前二年,在上海大东门,听了了愿法师讲完《金刚经》后,他决定出家了。我无法想象了法师讲经如何感人,只是后来,在九华山仁德法师的传记中,有一段文字提起了法师讲解《地藏经》地狱苦痛一节时,座下数百人痛苦流涕,无不动容。法师的摄受力由此可见一斑。
出家的第一站就是杭州,吃了几个月天堂里的米饭,他终于无法忍受没有面食的尴尬。于是,卷起铺盖继续寻找。途中经过南京时,看望了一位老乡,告知离他家住处不远的老山有座规模不小的丛林。
寺院名叫九峰寺,最初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不过,明代到是曾经出过几位禅师,在锦江等灯录里还依稀可寻当年的辉煌。
一住就是八年,农禅并重的生活尽管简单、重复与单调。在一般人眼中,甚至是寂寞、空虚与无赖的代名词。可是,在信仰者看来,即便只有清风明月、青菜芦菔,依然可以活出第一流的生命品质。
1955年初夏,老人离开九峰到上海亲近禅宗一代名宿来果和尚。住在静七茅蓬过夏,每日静香数只,间或来老提嘶一二。棒喝交参,正念日增。
闻能海上人来金刚道场开讲大论,遂每日不辍,闻思法要。讲席将终,欲往五台长期亲近海公。拜见之时,忍不住打听五台气候如何。海公智慧深广。答曰:“去后即知。”
每当和弟子们说到能海上人,老人总是透出恭敬的神态,忍不住在言语中赞叹不已。老人在清凉桥吉祥律院亲近上人三载有余,这期间的学修对于日后的僧侣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初到台山,就感受到律院严谨的道风与学风。上人每日登台讲法,各地学子们席地而拥,饱尝甘露。律院依照律制要求,受戒之后必须在寺学满五年,方可领取戒牒下山。
一次,传戒刚刚圆满。次日清晨,院内集众钟声骤响。大众闻声云集大殿,彼此打听出了何事。不一会儿,上师面带怒气出现。质问是谁破坏规矩,将戒牒发给新戒。大众一片寂静,参与其中的几个执事赶紧出来求忏悔。并说明,有些新戒由于年龄和身体等原因,不能住在此地学律。上人说:“把戒牒教上来。”不多久,陆续收回。
有个东北新戒,行武出身,在俗时候曾做过营长,忍不住在下面说:“老上师,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还墨守成规,你这么做不行。我们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不能强迫我们。”上人回答:“那把戒牒留下,你先回去吧。”话虽不多,但字字千钧。当时,老人刚到台山不久,这件事给他印象颇深,感受到律制的威严与摄受。
老人虽在禅宗道场出家,个人修学用的却是念佛一法。当时,在出家的寺院每天坐香,禅堂里的班首师傅讲开示,也常说起如果参“念佛是谁”的话头不相应,就先念佛,念久了,渐渐就会明白。实在说来,明清以下近几百年,佛教主要内容也就这些了。襌净合流,有教无观,不重律仪次第等等,对其在世间流传造成许多流弊。
老上师是藏传格鲁系的传承。所以在律院里,每天除了学习教理之外,还安排大量时间用于修行实践。老人在实践这块儿却还是守着自己的方式,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静坐在炕上默念佛号。面前放置一只小盒子,盒子打开后就是一尊精致的阿弥陀佛的接引像。当然,是他自己亲手绘制的,也是他心目中弥陀的样子。
不多久,他的这一举动便受到客堂知客师的重视。做为格鲁的道场,居然有人在里面念佛,知客师傅有点接受不了。听到有人反映,他来到老人的寮房,事实证明后,他觉得有必要向老上师反应。上师听后,轻声说:“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上师的造访让老人惊恐不小,下座顶礼一翻后,站在一旁准备接受质问。上师一边看着桌上的火柴盒子与佛像一边说:“就住在这里,安心修行。”丢下这句话,上师出了门。(写到这里,禁不住泪如雨下,惭愧自己无福,亲炙上师座前)。(未完待续)
汉传佛教,在宗派出现之后,彼此之间非但未能相互赞叹,诋毁的声音倒是不少。老人住台山时期,知道他专修念佛,经常有人找他校量各宗优劣。
一天,来了位禅和子。见面落座后,突然发难:“我们禅宗修行高,立地可以成佛。不像你们念佛,到了极乐世界后还要修无数劫才能成功。”
话音刚落,老人不紧不慢地回答到:“噢,你还要立地。我不立地就成了。”对方看在口水上占不到便宜,只好说:圆霖不弱。”
宗门末流,落于口头,不务实修,无怪五叶凋零,举步维艰。
当时,禅宗由于几位大德努力,也曾出现一时兴盛。来果老和尚中兴高旻寺后,晚年移住沪上静七茅棚。老人在茅棚住过三月,平时注意观察来老的语默动静,受益不少。
一日,从高旻寺来了位法师问候来老。寒暄过后,对来老说:“如今管理寺院和以往不同,需要和政府打交道,搞好关系,不能没有他们的支持。”言下之意,希望得到来老的认可。
来老是湖北人,说起话来有点地方口音,不过仔细听起来还是能听懂。老人就站在旁边,听到来老一字一字的说:“我持戒,龙天拥护;我参话头,诸佛赞叹。”
禅师就是禅师,字字斩钉截铁,决不拖泥带水,不容半点含糊。宁坐蒲团冻饿死,不将佛法做人情。
若干年后,老人也有相似的遭遇。
文革期间,他出家的寺院被毁。82年,他重回祖庭,着手恢复。一砖一瓦,亲力亲为。政府部门要他拿着化缘簿,一起去国内的名山大刹筹资。老人说:“可以可以,不过有个条件。首先要县政府带头,县委书记和县长先捐款,否则别人不会相信。”统战部的人看出来老人软中带硬,如意算盘就只好搁下。
目睹一些在旅游景区的寺院,遭受大量游客观光带来的负面影响。老人在修建寺院过程中,特意把殿堂建得普通一般,旅游含金量不高,有的地方还甚至显得破旧。倒不是没有建设资金,经常有海内外护法来山,表示愿意出资帮助重修殿堂。
遇到有人问到此事,老人总是面带微笑地回答:“我们这里是山中特色,我们又是山野之人,不要搞得太好,能有住的就行了。”他还幽默的说:“房子破点就容易看破嘛”!
是啊!佛陀时代的比丘,也只是树下一宿、日中一食而已。对照今天,我们在物质方面十分富有。可是,却常常缺乏一个出家人应有的东西——道心。
一段时期,经常有毛贼光顾寺院。老人以调侃的口吻对出家弟子说道:“最近到寺院里发盗心的人不少。”
一时哄堂大笑。笑过之后,引起大家更多的反思。
比丘啊!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到僧团?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做什么?
你是否为道而来?你能否坚持道心?你是否能为法忘身?
你为何默然,是对自己没把握,还是对三宝没有信心。
假如你做不到,那你就是在盗取十方的信施,你就是在骗取檀越的血汗。
比丘啊!问题摆在面前,每个人一定会有不同的答案。
我有次问起老人,在台山参学的情况,他谦虚地说:“自己不爱说话,常住安排当任堂主。”
堂主是丛林中四大班首之一,在两序中属序职。一般由道德修学戒腊俱优的僧人担当,为年轻的出家众做表率,同时指导学修。
在台山过完第三个寒冬后,老人离开清凉桥,再也没有回去过,也再也没有见过老上师。
可是,对上师的关注却一直埋在心中。80年代初,宗教政策刚恢复,老人在灵谷寺巧遇在台山一同学习的寂度、根通诸师,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上师走的时候怎么样。
老人常把上师的故事讲给弟子们听,其中有几个听多了,都能记下来。
上师未出家前,曾经在云南讲武堂任教,国家主席朱德曾经是他的学生。解放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上师德高望重,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朱德亲自到宾馆看望老上师,并询问有何困难。上师回答的非常好,“有困难的话,出了家就没有了。”
是啊!真正舍弃五欲,放下财色名利的僧人,于人无争,于事无求。世人所谓的困难,在他们眼里不仅不是问题,而且可以成为解脱道上的朋友。这就是在家和出家的差异,世间的人又有几个能明白呢?
所以,老人经常劝来山的居士和信众要念轮回苦,发心出家。他常说:“世间人享福,福过了就是气。出家人就不同,享的是清福,越品越有味道。”有时请他写字,他就写“布衣暖、菜根香,经书滋味长。”
一次,陪老人进城开会。在车上,对我说起他未出家的时候,每年眼睛都要害一次病。出了家之后,说来也奇怪,就再也没害过了。我知道他是在暗示我,我自小身体就弱,体质差,一般人都能看出来。
他经常拿上师的一个比喻来讲给信众听。上师在一次讲座中,针对有人混同佛教的善法与世间善法时,上师打了这个比喻。他对坐在地下的学生说:“你们要下山为常住买米,半路上遇到一个妇女。一手抱着个吃奶的婴儿,一手牵着个刚能走路的孩子。你是帮助妇女照顾孩子还是不管,继续去买米呢?
毫无疑问,肯定要把常住的事情办好,这是根本。世间善法不是不做,但要分清主次。就好比断烦恼,我们先要找到他的根,这样一刀下去,就能彻底解决。否则,在枝蔓上费了老大的劲,效果也未必理想。
每次,讲到老上师临终的那一刻。结跏趺坐,安然舍报,预知时至的时候,老人眼中透出更多的光亮。他认为,这是上师一生最辉煌的乐章,也是一个出家人一生修学接受检验的关键时刻。
老人很重视临终的境界,他一生持名念佛,每天弥陀不辍,发愿往生西方净土,手绘佛像万余幅。今年,他已经有95岁了。我想,他老人家的愿望很快就能够实现。
告别了五台,离开了老上师,下一站往何出去?
当时,一代禅宗泰斗、年近120岁的虚云老和尚已经驻锡江西永修的云居山。各地衲子仰慕老和尚的道德与修证,不顾山间清苦,每日劳动,布衣芒鞋,夜宿草棚,从四面八方赶赴云居。
消息传到老人的耳中,他想起和老和尚在上海曾有一面之缘。而且老和尚年轻时三步一拜、朝礼五台时曾在狮子岭过年。于是,一个人从五台来到了云居。
这时,已经是公元1959年初春。这一年,来云居山的出家人特别多。每天禅堂坐香,老和尚都要来讲开示。
老和尚不知从哪儿听说老人会画画,就派人把他叫到自己住的云居茅棚,要老人现场给他画像。老人后来回忆时说到,老和尚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大约用了半个小时,第一稿出来。老和尚看了后,觉得不太像。老人说就再画一次,虚老说你靠近点,这样看的清楚才好画。这一次,用了一个小时,画好后递给虚老过目。老和尚一边缕着山羊胡子,一边点头称赞。同时,还吩咐当时的侍者拿水果招待老人。
接下来,虚老又给老人一个任务——将历代祖师道影画出来。
住了三个月,老人决定返回出家的道场,看望昔日的同参。临行前,向虚老告辞。老和尚问:“怎么要走呢?”老人只好回答:“没有粮票了。”老和尚说:“要啥粮票,就在这住。”老人没有接受挽留,最终还是下了山,回到了狮子岭。
又是一次诀别,若干年后,回忆起来,老人还引以为憾,后悔未能在虚老身边陪他度过剩下的最后几年。
他常提起虚老如何送人的情景。有人向虚老告假下山时,老和尚总是站在门口,目送着行人,直到人走到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他才回寮房。
那天,老人下山的时候,虚老同样站在老地方,眼光中充满了慈悲。老人在拐弯处,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眼,令他终生难忘,也使他受用非浅。
三十年之后,因缘的际遇,老人住持狮子岭兜率寺。在祖堂的中央,他亲手塑了一尊虚老的坐相。这样,他每天就可以礼拜老和尚,亲近老和尚。
在云居期间,有位师傅送给老人一只虚老曾经使用过的布质蒲团。他一直视为珍宝,即便在文革那么动荡的日子,他也保管在身边。
老人曾手书虚老撰写的一幅对联,挂在狮子岭的藏经楼上。“尘外不相关,几阅桑田几沧海;胸中无所得,半是青山半白云。”那是虚老,一位开悟禅师的境界,也是他自性中的流露。
是啊!能够身在红尘中,却不为世间的物欲所惑。笑看人生风雨,体味无常本质。心中不留痕迹,与山水做伴,共自然为友。清风明月,皆是本来面目。翠竹黄花,尽显本地风光。
虚老做到了,我不知到,我的师傅做到了没有。
兜率寺位于南京江浦老山的狮子岭下,传说地藏菩萨在此曾静坐一夜,次日后山上的石头全都凸起,很象他的坐下的狮子的模样,所以寺院又名狮子岭。
寺院年代并不久远,最初是明末当地一位叫白庵的秀才,由于反对清朝政府,隐居山中学佛时修建了一所很小的茅庵。后来,历代僧人随力修补。在清末民初,由于当时高僧法一上人的住持,寺院达到鼎盛。常住僧人数千指,常年传授大戒。
当时,禅和子中间流传着一句话:“上有文殊宝光,下有金山高旻,中有狮子岭。”
许多禅堂的老参们晚年均选择那里作为归宿,狮子岭在当时成了著名的养息道场。一段时间,金山高旻的老修行住了不少,每日做香,出坡,解放前有近100人。
师傅的师傅是狮子岭的首座,上体下意老和尚。我没有亲眼见过,只听说他年轻时在金山禅堂担任班首,想来功夫不会太弱。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多的了解,解放前两年,师傅在师公座下落发,在狮子岭住了8年后,外出参学。不知不觉,外出四个年头,听说有的地区对出家人活动有限制,他决定回去看看。
这一次回到江浦,他基本上就再也没有离开老山,他几乎把自己的生命交付了这座连绵百里的山脉。所以,老人晚年自号山僧也是由此而来。
一直觉得自己和山有种微妙的因缘,自己的俗名与法名中都有山,剃度师号山僧,后来学法的师傅号山人。在平地上走的不快的我,一旦到了山里,情况马上会转变。师傅也是这样,他不习惯进城,所以一生都住在山里。
回到寺院不久,国家遭受到来自自然和人为的双重考验。三年的自然灾害,寺院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没有多余的粮食,出家人每天只能吃到三顿稀粥。所谓的粥,实际就是一小把米熬一大锅水而已。
师傅有次说:“那时候他负责行堂,有位师傅一顿饭喝了八碗粥也无法解决肚皮问题。”听了以后,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不知如何回答他。他们那代出家人,经过的事情太多了,承受的考验与磨难也太多了。修行必须经历境界的考核,所谓“不经一方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今天的出家人,早已摆脱了道粮的压力,不用为三餐操心。可是粥来面去之中,能否保持一种知足与感恩,能否心存五观。我觉得,我要好好反思一下了。
刚刚度过饮食的难关,政策的高压又接踵而来。政府工作人员三天两头来山上,逐一找年轻僧人谈心,劝他们回家,并允诺还俗后可以安排工作。一些人对于前途茫然,因此下了山。也有一些老师傅们没有动,我的师傅选择了留下。这是生命的承诺,这是对三宝的信念。
我有时在想,如果当时让我来选择,我会何去何从?
来山的人越来越频繁,空气也日益紧张。留山的师傅们管不了那么多,每天依旧出坡参禅。在他们看来,一句“念佛是谁”的话头比什么都重要。只要内心安稳,天下就会太平。
一天清晨,下了早殿过完堂,师傅们在院子里经行,听到山下有汽车马达的轰鸣声。这么早来山,一定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前几天,他们来过,找方丈和尚谈话,不知说了些什么。不过,似乎还很客气,称和尚为了成法师。可是,不知为何,大家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对劲。
果然,过了几分钟,院门口一下子冲进三五十个荷枪持弹全副武装的军人。在为首一个军官的指挥下,把师傅们包围住,几个年轻的用一指粗的麻绳把了成和尚反捆了起来。前两天来过的那个人这时扯着嗓门大叫:“了成因为反对政府,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现在奉命逮捕归案。”说完,拉着人就往外走。
了和尚一边走,一边看着被吓呆的僧众们大声说:“师傅们,不要怕,把话头提起来,将功夫照顾好,千万别打失了。”了和尚这句话,似狮子吼,大家为之一震。
开悟的禅者,即便千军万马、大敌当前,也能保持一种从容不迫,也能拥有一颗明明觉知的心。
过了几个月,师傅在南京遇到了和尚,问到被抓后的情况。
了和尚说:“他们在吓唬人,到了山下就把绳子松了开来。在牢里呆了几个月查不出问题,只好放人。”
60年代中期,政府组织南京出家人中的骨干在当时佛协所在地毗卢寺开学习会。少数几个出家人为了迎合当时的政策,也出于保护自己,在会上对佛教及昔日的法门兄弟展开了诋毁与谩骂。
一个人为了表明自己的觉悟,在台上大谈佛教的问题。了和尚在下面听了半天,突然冲着那个人说:“做人要有良心,吃着佛教的饭,还要骂佛教,能算是出家人吗?”
那人一时激动起来,扯着脖子大骂:“了成,你也不是个好东西。”话音刚落,突然说不出话来,在那里痛苦不堪,在场的出家人嘴上不讲,心中都认为这是现做现报。
在那个黑白颠倒、父子反目的时代,这些事情屡见不鲜,层出不穷。
做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不能知恩图报也就罢了,还要反戈一击。愚痴的人啊,难怪佛陀要称你们为可怜悯者。
政府干部三天两头来做思想工作,介绍国家政策,劝人回家。
狮子岭的师傅一天天减少,最后只剩下几个年老无家的。
一天晚上,老人和来自东北的安西师谈到半夜。
第二天,下了早殿,两人向几个老师傅告别,又到祖塔顶礼三拜,随后下了山。
来到山下,他们照着昨晚商量好的计划,来到老山山背的星甸,这里山脚下有个废弃的小庙,叫地藏寺。已经有几年没人照料了,上次老人和安西师曾路过此地。他们想在这里,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
地藏寺岁月
一个小庙,两个僧人,三支静香,晨昏两堂功课,平淡无奇中却蕴藏着无限生机。
离开丛林,又处在动荡的年代,衣食住行都必须自己解决。来之前只带了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和几斤大米,过了没一周,米袋子就空了。
寺院没有信徒来,又不允许外出化缘。吃什么?民以食为天,五脏庙里的菩萨们一刻也不能得罪。
两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得出个结论。还是走老祖宗的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毛主席还教育我们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呢!
地藏寺紧挨着山脚,靠山吃山,守着宝山正好利用。
第二天,清早起来,喝口水,老人带着准备好的斧子和绳子独自上了山。当然,大树是不能砍的。这一点,出家人比谁都清楚,戒律中有明确的要求。那就拣那些已经死掉或者枯掉的树吧,反正在大山里,只要肯跑,半天下来总不会空手而回的。
山林里的出家人,自马祖建丛林后,每日出坡劳动,习以为常。在劳动中培养简朴的生活方式,在劳动中锻炼身体,在劳动中磨练品质,在劳动中体验禅的境界。
所以,后期有的禅宗的祖师们在劳动中开悟:香严收拾菜地,扔乱石击竹悟道,于是有挑水砍材皆是道的说法。有一首偈子描述的十分恰当:“佛法融融万法融,真真假假在其中。”
直到现在,老人住持的兜率寺,僧人不论老幼,每天依旧要出坡劳动。
准备好约有一担材,就赶紧挑下山。分量也着实不轻,怎么说也要有七八十斤。后来听老人讲的时候,我想想腿肚子都有点抽筋,不用说亲自去挑了。
这时,安西师在寺院烧好了开水,还诵完了部经,又倒出一壶水放在桌上凉着 。等老人一到,连忙接过材,换在自己肩上。一边说:“快喝口水,歇息歇息。我去镇上把柴火换成粮食,你等着吧。
老人几杯水下肚,才觉得肚里咕咚咕咚,一天没吃东西了。“出家人要忍饥耐寒,安贫才能乐道”,他想起做沙弥时候自己师傅经常这样教诲。
于是,拿起念珠,盘起腿子,念起阿弥陀佛的圣号。
临近中午,听到安西师从外面进来的脚步声。边走边说:“圆师傅,今天收获不小。你砍的柴火很受欢迎,又干又熬火,全都被抢去了。换了二斤米、一斤油还有些蔬菜。
两个人都很开心,这下道粮的大问题解决了。
于是,每天清晨,老人总是准时上山、准时下山。安西师也是准时上镇子,准时回来。
一天傍晚,突然下起了大暴雨。持续到第二天早上,没有停的意思。寺里的米和菜都吃完了,两个人约定,就烧点开水当做早饭。开水烧好后,先倒出一杯,供养佛陀。
雨下得很大,门外有人猛烈地敲门。这么早,有谁会来?带着疑惑,安西师打开门,看见一个中年男子提着个布袋站在雨中。
“有事吗?”安西师问。
“我是不远村上的,听说这里来了两个师傅,早就想来看看,一直没空。今天想一定要过来,这是点米,供养给师傅。”说完,递上手中的布袋。
安西师知道这袋米的份量,走到里面告诉在打坐的老人。两人彼此更坚信只要肯修行,三宝就不会舍弃他们,就一定会护佑他们!
老人喜欢写字画画,幼年的时候,在乡里随乡里几位画师学画,工笔素描,临摹字帖。
稍长,又外出拜访名师,并从当时一些大家,如黄宾虹等人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其后,游历山水,师法自然,念佛参禅。晚年以后,下手无烟火,落笔现恬淡。处处现景,般般现前。
出家后,常年住在江浦县。江浦县城地方不大,据说历史上县太爷公堂上打板,四个城门都听见声音,它的小巧可想而知。江浦近代出了个名人,爱好书法的人都不会陌生,他就是被公认为当代草圣的林散之先生。
老人和林老的交往从解放初期开始,那时二人都在中年,创作的高峰期。林老生平喜山水,经常到离家不远的狮子岭小住,体味山林的静穆,激发个人的书画灵感。每次来山,总免不了与老人切磋书艺,畅谈画术。
老人有时画了些得意作品,也乘到县城办事,顺便带给林老分享。老人很尊重林老的人格,在和别人提起的时候,经常赞叹不绝。文革期间,老人有次和林老约好一同去汤泉下面的林场写生。两人搭乘下乡的公交车到了路口,问清驾驶员下午四点末班车回去。
林场的风景把两位吸引住,也把积压在内心的忧虑一扫而光。一僧一俗从上午画到下午,不知不觉到了回去的时间。林老发现时候不早,赶紧提醒老人往路口走。回头一看,老人在远处树林拾柴火。他边叫边往外跑,老人背着柴火也快步跟上。
到了路口,林老表情严肃的说,“走了走了,刚刚开走了。”
“那咋办?”老人问。
“慢慢走回去吧”林老不急不缓的说。
老人每次介绍这件事情的时候,眼里闪烁着一种精神,我想那是一种随喜。
老人在文革期间,偷偷为林老画了一幅个人素描。后来,画不知怎么到了朴老手中,朴老敬慕林老的人品及书法,特意在画上题字赞叹。
老人母亲往生之后,林老得知消息后,特意前来吊唁。并手书碑文,以为纪念。
文革后,林老移住南京,两人见面机会不多。可是,每次林老回江浦或者老人到南京开会。二人总是要找机会见面,一叙友情。
林老一生未皈依佛门,临走的时候,写下四个字“念佛升天”。
不知到林老会到哪里,也不知到何时再来。
可是,自那之后。林老的后人每年总会来狮子岭,看望这位和他们的祖辈要好的老和尚。
席卷全国上下的文革热潮,从城市蔓延到了乡村。很快,又波及影响到地藏寺里二位清修的僧人。安西师拿定主意,决定回东北老家。和老人分手的时候,两人相互对望了半天。这次,没有从兜率寺下山的彻夜长谈。他们也不知道,分手后何时还能再见。
老人,没有离开江浦。当地政府,把他安排到老山林场。老山位于南京江北,连绵近百里。老人的人缘好,林场里的上下对他还不错,尽管知道他过去的身份,可是乡里人朴实,并未对他歧视,另眼相待。
林场有片桃园,在山那边,周围环境很好,还有泉水流过。不过,位置比较偏僻。加上老辈人传说,桃园中闹鬼,所以没有人敢去看管。所以,这个任务只有同样是“牛鬼蛇神”的老和尚来承担。
桃园在老人看来,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偌大的一片园子,除了他自己外,见不到人的踪迹。间歇,飞过几只小鸟,停不到几分钟,耐不住冷清,也结伴离开。
清晨,老人把藏在屋内横梁上的《金刚》和《愣严》取下来,揣在自己特制口袋里,挂在贴身衣服内。左手提瓶开水,右手拎只篮子,里面放二个馒头,一点咸菜。
到了桃园,找个隐蔽的,外面不易看见的地方,坐下来。老人小心翼翼、恭恭敬敬的取出经典,坐在地上读诵。渴了,喝口开水,饿了,就着咸菜嚼馒头。
一天、二天,几年下来,不知觉,老人对于二部经完全熟捻于心。根尘交触时,境界显行处,般若与三昧的光明时常启发。
一次,坐下去一会儿,睁眼已过了半天。越发坚信世间万象,当体皆空。时空假有,因缘乃生。
林场的同事见到这个不吃肉、没有妻儿的老头子,觉得很奇怪。有次,几个喜欢多嘴的年轻人找到老人。来之前,他们做好了准备,要和老人辩论,狠狠批批老人的封建迷信思想。他们问起老人为何不结婚又不吃肉?
没有和他们介绍佛法的道理,老人只是轻描淡写的回答:“和尚不成家,把老婆让给你们。不吃肉,将计划留给大家。让你们得到利益,难道还不好吗?你们整天说为人民服务,我们信佛就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一句话,出乎大家意料。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面红耳赤,慌忙中连招呼也不打就跑掉了。
一晃四五年,外面的世界如何,老人一概不知。在他看来,只要内心平静,自己的天下就会太平。
后来,与别人谈起那段岁月之时,他总是感叹,那是自己最用功的时间。没有外缘干扰,没有内魔逼迫,每天向佛陀请益,与自我对话,同山林交流,对流泉相映。
“日子过去了之后,才知道是最好的日子,”老人曾对我说过这句话,我听了后,明白不了。
写到这里,我理解到,原来老人要我快乐的接受眼前的一切,无论是风还是雨。
60年代的最初几年,天灾人祸,中国遭受到严峻的考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当时,老人由于绘画的特长,被安排到宣传部门,帮助画些大幅标语和宣传画,每天吃饱肚皮倒是没有问题。
几个月没收到家信,到处传说饿死人的消息令老人心中颇为不安。一天,老人用平时省下来的全部粮票买了三斤面粉,装在一个布口袋中。回到单位后向领导请几天假,打算回老家看望父母和亲戚。
出家后,老人没有回去过,不知觉,都快二十年了。不晓得父母亲现在如何,着目前的情况来看,能健在就阿弥陀佛了!老家本来就不富裕,兄弟也小,两位老人一辈子操劳也不容易。一路想着,火车来到了宿县火车站。
这里,老人很熟悉,在家的时候经常路过。
可是,今天却似乎和往日不同。火车站周围冷冷清清,没有了昔日的热闹与喧哗。路上的行人一个个没精打采的样子,有的人脸上名显的浮肿,极个别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恐怕一阵微风吹来,也招架不住。
老人有些紧张,家乡的情况看来比想象中还要糟糕。镇上都如此了,父母住的乡下,可能会更恶劣。想到这里,心里更加担心,口中不觉念起了观音菩萨的圣号。
来到村子边,刚好是午后,看不到也听不见一点生机。老人决定等天黑了在回家。他在村子外面呆了半晌儿,天完全黑透了,一个人摸黑进了村。到了家门口,敲了半天,里面有人问:“是谁?”
“是我”
门开了,老人俗家的妹妹站在门后。看到老人,凹下去的眼眶里冒出一丝精神,忙招呼往里让。
内屋靠墙,两个小孩子围着桌前,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不时还捧起碗喝一种绿色的液体,看上去,进来个陌生人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投入。
老人在桌前坐下,突然觉得腹内空空,问妹妹还有什么吃的,对方回答有的。
跑进厨房,掀开锅,老人也跟上去,眼前出现了一湾绿水,上面飘着几片绿叶。那东西老人非常熟悉,是山芋的叶子。
想哭,那玩意一般是喂猪的,现在……
他顺手盛了一碗芋叶汤,回到座位,两个孩子还没有吃完。
看着透不出一点血丝的小脸,老人不知说什么。
他从贴身的衣服中把口袋掏出来,将外面的报纸一层一层剥开。两个孩子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好奇地看这这个穿着奇怪的人。
见到面粉的一瞬间,孩子们的眼睛亮了起来,那种感觉就象今天的困难儿童登上天安门城楼。
老人往每个人碗里抓了一小撮,就着芋叶汤,两个孩子拼命地喝着,不小心落在桌面上的一点,也用手粘了起来放进嘴巴。
老人一边看着,一边在心里发愿,如果可以让所有的人免除饥饿,自己宁愿饿死。
过了几天,老人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故乡。
过去就让他过去
人是很奇怪的,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以损害任何人,即便是自己的同胞与手足。
老人回到寺院不久,佛教协会听说后,派出人来查看,询问相关情况。真慈法师当时任佛协领导,给予寺院关心不少,老人经常提起。对于那些在困难时期帮助过自己的人,老人总是记着他们,经常挂在嘴边。
八十年代初期,老人收到圆澈法师从北京的来信,提到中佛协要在北京召开全国会议,提名代表时候把老人也列入在内。询问老人何时到京,以便联络。
老人和圆澈法师是同参兄弟,当时在上海,两人初次见面后,圆澈法师一定要和老人结为同参兄弟。 在五台山的时候,两人曾经共同亲近海公上人。之后,老人回宁,文革开始后,就再也没机会见面。
听说老人重返狮子岭,园澈法师特意顺路来拜访过。故友重逢,促膝长谈,之后,圆师还写了首小诗以为纪念。这次,借着中佛协开会的机会,他们又可以老友相叙了。他还担心老人住的地方偏僻,通信不便,所以特意提前通知。
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老人一直没有收到来自北京的通知。直到有天,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告诉他,他的那个名额被另外一个人顶去了,要老人去找那个人评理。老人轻描淡写地说:“他想去就给他去吧,过去就让他过去,还有什么值得再计较的呢?”
经过一生风雨的老人,对事件的名利得失早已看的很淡。
做为一个比丘,应该忙碌追求的是什么,他已烂熟于胸。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老人心中最清楚。还是那句话:
“过去就让他过去?”
天终于亮了
20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气候温暖。宗教政策全面落实,也给老人带来了生命的活力,尽管当时他已经年近古稀。这年四月,老人约了几位昔日同参,回到阔别二十年的狮子岭。
昔日的寺院,却被掩埋在荒草之间。瓦砾碎砖,散落在各处。唯保留有老大殿——兜率宫和老禅堂,据说,那是由于留给几只水牛做了牛棚的缘故,才在浩劫中幸免于难。里面的牛粪,东一堆西一堆,让人无处下脚。
“法轮未转,食轮先行。”恢复道场,非一日的工夫。先把斋堂建好,倒是刻不容缓。二十年后,老师兄成忠回忆起寺院刚恢复修建的那段日子,依旧还是历历在目。
当时,没有厨房。大家烧饭就在空地上,用几块石头垫着,上面架个锅。山上拾些树枝,水塘里舀些水。吃饭时间一到,大家就随手拿块石头,坐在上面,一边吃一边谈论修房子。
那时侯,隔三差五就要到山下18里外的高旺镇上,买些挂面回来做为日常的饮食。直到后来,来山居士们多了,大家自发供养粮食,才不用再买了。
兜率宫位于整个寺院的最高处,也是兜率寺的主殿,打扫收拾干净以后,里面空空荡荡,佛菩萨像全部毁了,得想办法解决。这对老人来说,并不太难。
就地取材,山上取了些适合雕塑的粘土,在临时搭就的佛台上,动起手来。没几天,弥勒菩萨居然坐在了台子上,坦胸露跣,笑容可掬,好象预示着一个好的缘起。
老人写在纸上的对联,贴在柱子两侧。美其名曰,山里风格。
三圣殿在兜率宫的东面,面积不大。殿内东西两边靠墙横放着一溜排的玻璃框,里面是老人亲手绘制的莲宗十三祖师的道影。
据说,当时应苏州灵岩明学法师的的邀请,画了三套。一套赠送灵岩、一套由台湾某道场供养,余下一套安置三圣殿内。我曾亲眼目睹十三位祖师的道貌,其他的十二位,没有见过,不敢评价好坏。印光大师在照片上看过,对照画像,如出一辙。特别,绕佛途径印祖面前,妄想多的人,不敢开眼对视。惟妙惟肖,可见一斑。
那些日子,白天盖房子,常住的师傅居士全都出动,一个不漏。
“诸方禅悦浩浩荡荡,老僧这里,干活念佛吃饭。”老人这么解释。
晚间,大众集体到三圣殿内共修。坐香、听经、礼拜、忏悔,春夏秋冬,寒暑不废。
老人尝引莲池大师偈语告诫众弟子:“世间之事如钩锁连环,没完没了,苦不可言。莫贪五欲,赶紧放下,老实念佛!”
寺院围墙后有一棵四五百年的银杏树,三四个大人都抱不过来。一天,来了个东北居士,在寺院住了些时候。爱在树下乘凉,有天随口吟出首小诗,倒也是老人的真实写照。
一山一寺一老僧,一屋一榻一盏灯
一书一画复一塑,一心修得一寺成。
初次见到恩师不是在狮子岭,94年元旦后一天,搭乘一位居士的便车拜访老人。到得山来,有人告知老人去了山后的精舍。午饭在寺院吃的,饭后驱车前往汤泉,老人居住的处所。熟悉的孙居士介绍,那里是老人文革期间曾居住过的地方,现在房子由他俗家的弟弟住着,老人的房子依旧保留下来。偶尔,他回去住几天。
车在山里左右绕弯,生性晕车的我,希望早点到达目的地。开进山脚的一个院子后,车在一排普通的红砖房前停了下来。
大家下车后,跟着孙居士走到一间独立的两开间平房前。门开着,冬日午后的阳光正撒在屋子正中。一位穿着灰色大褂的老和尚坐屋子在中央偏左的地方。看的出来,他的精神很矍铄,身体也硬朗。看见来了客人,忙招呼大家坐下。
老人说话不快不慢,略有地方口音,需要仔细听。听说同去的人中,有的想皈依三宝,他把几个人带到里屋的佛堂。叫三个人跪在拜垫上。我在最右边,时间不长,可是忏悔、三翻羯磨、发愿却一个不落。
做好仪式之后,老人还给大家讲了半天。说了什么,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起他说我只是你们的证明人,就好比入党介绍人一样,三宝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要向佛学习。
送我们出来的时候,老人还提醒大家别练气功,又对我鼓励说:“你的个子最高,将来一定成就最大。”
口中说着再见,感觉老人特别慈祥。
月底就是春节,也许是和老人的宿缘,决定到狮子岭过年。为了这件事,我还特意一天中骑车一百公里到寺院和老人打招呼。听说我的想法,他没直接回答。只是一再说寺院里的饮食条件太差,可能无法适应。我表态没有关系,既然决定来,物质就不是问题。临走的时候,老人给我拿了只苹果在路上吃。
腊月三十清晨,天气阴沉,家家户户忙着过年。一路上,没有感受到节日的喜庆。这是生平第一次离开家过年,并且在一所山林的寺院里。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乘车在一个叫高旺的镇上下了车,没有公交,走了2小时,下午14点,我终于到山。 老人的屋里站了几个人,老人在用黄纸写牌位。给他顶礼后,招呼我坐一下。看来他很忙,说起经常在寺院发心帮忙的胡居士夜里往生了。儿女们满足她的愿望,把她送到寺院来火化。
我和老人一起下到化身窑的时候,胡居士已经被其他人放进了用砖砌就的火花窑,又用砖在外封上。半月以前,我第一次拜访老人从汤泉回去的时候,她还搭乘我们的汽车。熟料就这几天,就撒手西去,西北风越刮越猛,我有点冷。
封龛仪式时间不长,之后,胡居士的儿女们回去,我陪老人回寺。看出来,胡居士的死对他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几十年的修行,见得太多了。晚饭,是在厨房里吃的。一张小桌子,上面放了几盘中午剩下的菜,馒头几只。老人坐在中间,总共7个人,4僧3俗。饭吃的很快,没有在家人那么多葛藤。
在山过了两天,说实话,山上生活简单、寂寞,我没法适应。初二上午,我决定下山。和老人告假的时候,他不让走,坚持要我多住几天,我答应过些日子再来。
从那之后,每隔一段时间都上山住几天。一次,老人说:“来这里长住吧,不要你做事,专门看管藏经楼。没人时候自己读经,有人就出来接待一下。”
小时候,很羡慕出家人,尤其坐在水边林下,诵经禅修,更令我神往。
老人说了两三次,我想得好好考虑考虑。
八年后的盛夏,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给老人一个答案。
尽管,我没有常住在山。可是,我的根早已留在那个地方。
不知从哪一天起,来狮子岭的人渐渐多起来。有信徒、有游客,有慕名过来的,也有顺便撞上的。
来的人,大都有个心愿,希望得到老人的墨宝。
情天如此,雨天如此。清晨如此,夜晚如此。上门如此,来函如此。亲自如此,托人如此。
不分男女,不管贵贱,不计较信仰,不过问索画的动机。只要开口,只要自己能动手,老人一定是有求必应,从早忙到晚,一张一张从小屋里留到千家万户。
老人为人写字画从不收取一分钱的报酬,赔上笔墨纸砚那是常有的事情。
弟子们不忍心,就在门上写个告示:“中午12点至13点为休息时间,希望大家不要影响老人。”
可是,小屋还是常常被从城里赶来的信徒围个水泄不通,直到满足大家的愿望为止。
每次回师傅身边,只要看到他寮房外的陌生人,那十有八九是来索取字画的,老人为此也欠下不少字画债。